「3+1」個女人的人生故事 呂秀蓮
每個人都有故事,每個女人更有她說不完的故事。但故事怎麼說?誰來說故事?效果可能就不一樣了。
「這三個女人」的故事,是三個大學同班最要好的女同學在畢業十年之後,她們各自的生涯發展。愛情與婚姻是她們的故事軸線,但因為性格不同,人生觀有別,際遇更殊異,所以畢業十年之後,每個人的禍福喜悲自然完全不同。
結婚、單身與守寡是這三個女人的不同人生際遇,有部分出自個人的抉擇,但命運因素也很高。遇事抉擇的時候,考驗的是一個人的人生態度和價值觀,譬如愛或不愛?或取或捨?不過,一旦命運之神施展法力,你連思考都來不及,福禍就來臨了。所謂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一旦來臨,就得面臨。
尼采說:「弱者,妳的名字叫女人!」傳統社會中,女人在男人面前裝弱比較能獲取男人的憐惜。但沒了男人的女人,或者不需要、不在乎男人的女人,她也就不再是弱者了。
天上下大雨的時候,母雞就會撐起雙翅,把小雞們團團圍住,雨停後,抖抖羽毛,母雞收回翅膀,小雞們又重新蹦跳起來。然而有誰看到這個時候的公雞在做什麼?
許玉芝,高秀如和汪雲這三個女人,是我的朋友,是我自己,更是妳自己和妳的朋友們。這篇小說在自立報系連載期間,很多讀者說,妳寫的是某人的故事嗎?媒體界尤其自以為是地認為高秀如就是我自己。我的答案是,也不是。無論是或不是,其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們的故事帶給你怎樣的啟示?讓你對女人增加多少認知?
本書是小說,不是傳記,這三個女人是我杜撰的故事。那是一九八○年春夏間,我因為美麗島事件被捕入獄,在景美軍法處看守所?押偵訊。長達一百天日以繼夜的折磨之後,整個人失魂落魄,不止不成人形,內在心靈早已支離破碎。偵訊在除夕夜結束,熬過慘淡悲悽的農曆年,立即面對十天的世紀軍法大審判,其間發生慘絕人寰的林義雄母女血案,我頓覺天崩地裂,肝腸寸斷。
一九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軍法大審結束,我們重被鎖在不見天日的押房裡,四壁徒然。一方面因為不必再面對面目猙獰的偵訊員,心情稍感鬆弛,另方面卻也因為無人可談,無事可作而陷入另外一種發慌、恐「瘋」狀態。終於我想到用腦思考,用手寫作以打發歲月的點子。徵得獄卒同意,替我代購了紙張和原子筆,因為沒有參考資料,最好的辦法就是搜索枯腸,在記憶中捕捉拼湊長年從事婦女運動所積累的人生故事。
押房裡無桌無椅,我就坐在榻榻米上面,背頂著牆壁,把塑膠臉盆翻轉過來,用雙膝頂住臉盆底面,趴著身子寫作起來。有時累了,就到押房內的抽水馬桶蓋旁書寫。
這三個女人的故事,其實是四個女人的故事。「3+1」的故事,有血有淚,也有歡笑和驕傲。讀透她們的故事,也就差不多讀透你的人生。
謹將此書獻給天下的紅男綠女們!
也謝謝聯合文學出版社讓它在二十三年之後,三度問世。本書第一次出書是在一九八五年八月由自立報系出版,第二次是二○○○年十二月由草根出版社出版,併此致謝。
二○○八年五月七日於總統府
往日情懷舊夢溫 呂秀蓮
自從一九九一年回復因美麗島事件被褫奪了十二年的參政權以來,我歷經三次選舉,先後當選一屆立法委員、兩屆縣長,中間還擔任過一年的總統府國策顧問。由中央到地方,由外交而內政,生涯變幻不可謂不大。
政治是既忙碌又庸俗的工作,雖有心多從事怡情養性的事,總覺心餘力絀。文學和藝術是我的眾多愛好之一,但從政的日子裡,卻只能望梅止渴而已。然而,越是忙碌,越怕庸俗,因此腦際常閃出一個念頭:「待我縣長任期屆滿,我要退休,舞文弄墨去也。」
我迄今出版了十三本書,其中最特殊的是在獄中寫就的兩本小說:《這三個女人》和《情》。前者於獲釋歸來的八五年由自立報系出版,後者於翌年承楊青矗兄經營的敦理出版社出版。我原非文學中人,但這兩本小說出來之後,倒曾引起文學界一陣好評。讀過《這三個女人》的女人,都會在書中看到屬於自己或屬於自己的女性同胞的故事,而讀過《情》的人,應該也會眨著潤濕的眼角,憶起我們曾經一步一腳印走過來的有點兒悲愴,又有點兒溫馨的往日情懷。
轉眼十二、三個年頭已過,在這段時間,台灣的社會和政經情勢產生莫大的變革。報禁解除,報紙張數也擴增,而電子媒體和電腦網路尤其蓬勃,其結果,文藝副刊和文學創作難免落寞。偶爾我會想起我書中的各種人物,很想替他們編織後續故事,但下意識裡又覺得,即使我寫了,又有誰在乎呢?
沒想到不久前,忽然收到前衛出版社林文欽先生的傳真,問我願不願意將這兩本獄中小說讓他再版?前衛是台灣出版界捍衛本土文化的尖兵,多年以來為台灣的政經文史出版許多好書,培植許多人才,我的《新女性主義》、《兩性問題女性觀》以及《重審美麗島》三書,皆由前衛重版問世。如今林文欽先生又對我的兩本獄中小說有重版興趣,我高興都來不及,反正兩本的出版契約期限早逾,能讓它們跟前衛的「台灣文學名著」諸多佳作並列,讓讀者朋友陪我重溫舊夢,豈不開心?
這兩本書若能獲得您的青睞,也許,我真要認真考慮退休下來,去寫小說,去寫這三個女人跟李正宗這一家的後續故事了,而他們的故事,其實就是你我的故事。
原載於二○○○年草根出版社《這三個女人》
再版的話 呂秀蓮
一個不曾寫小說的人寫起小說了,跟一個不曾看小說的人看起小說了,不知何者較有意思?自從《這三個女人》中篇小說在《自立晚報》連載以來,有些朋友對我的越俎代庖不以為然,倒是我頗為法律界與政治界多位從來不看小說,卻因著我而每天關心《這三個女人》的朋友們,默唸一聲:阿彌陀佛!但願我沒有倒掉他們對文學偶生的胃口,但願原本愛讀小說的朋友不會因此而不再看小說。
事實如何,我不得而知。但這本書八月八日中午出書,《自立晚報》將它上市甫十日,就發現倉庫裡只剩下一本了,買書的與賣書的,為此同樣發急,而身為作者的我,自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經過五年三個半月的與世隔絕之後,居然發現我尚未給社會全然遺忘,而且發現原先愛我的人依舊愛我如昔,尤其一些本來不了解我的人也有了較為正確的了解,我能不感到溫暖,感到慰安麼?
想想看美麗島事件後,報章雜誌如何充斥著對我個人的誹謗與對新女性主義的誣衊,聽說某位電視播報小姐還乘機捏製了一頂「性開放」的黃色帽子亂扣人,氣得我的新女性同好們直想把電視機砸掉。其實遠在這之前,打從我提倡新女性主義十四年以還,我便經常要擔待莫須有的罪名,承受莫須有的指摘,擔待久了、承受夠了,我自然養成「笑罵由它,好事我自為之」的德性。有位記者先生在他的採訪中說過,那些處心積慮想打擊呂秀蓮的人,如果看到她氣定神閒,泰然自若的樣子,一定會對自己的咬牙切齒、摩拳擦掌感到索然無味。
也許他應該說:如果那些漫罵侮辱的人,肯於平心靜氣地了解新女性主義的內容,他在發現所漫罵侮辱的根本不是新女性主義的主張之後,一定會為自己人云亦云、無的放矢的盲目衝動而深深汗顏!
譬如那些以為新女性是男人的仇視者,是婚姻的否定者的人,當他看到許玉芝如何在自我掙扎中細心維護她的家庭,高秀如既享受獨身的樂趣,又不忘了覓索靈魂的伴侶,以及汪雲經過婚變與喪偶的打擊而後醒覺時,對失貞的亡夫仍存念著繾綣情愛和理性的寬懷,他還有什麼好緊張、好痙攣的?不止這三個女人,本書收錄的其他三篇小說中,幾位具有男性沙文主義氣質的男子,我也不忍過度描抹、攻擊他們,毋寧視之為謬誤的兩性社會的共同受害人。抑有進者,我在故事中還一再用心地刻繪心地寬廣、性情朗落的新男性人物。
又譬如那些以為新女性是懶怠於家務、厭惡乎庖廚的人,當他聽到這三個女人吱喳絮叨的domestic細述,無論是許玉芝對與圍裙和尿布為伍的喃喃怨言,或者高秀如對烹調作羹湯的自得其樂,他在難耐其嚕嗦煩瑣之餘,是否應該捫心自問自己又何曾熱中過家務,精通於煎炒蒸煮?至少當你發現我本人常汗涔涔待在廚房,並且香噴噴熱騰騰端菜上桌時,請別大驚小怪,故作恭維;早在九年前,我舉辦男士烹飪大賽的同時,就標榜起「左手拿筆桿,右手拿鍋鏟」的新女性了。
再譬如那些攻訐新女性主張性開放、提倡雜交群婚的人,當他讀到高秀如因著她所心儀的男同事有過不負責任的性放任而怫然否定他時,難道悟不出新女性對「性」的莊重態度?在舖陳高秀如卓爾不群的生命中,我穿插著一個婚前失貞以致命運坎坷的少女故事,難道不是在對性道德作愷切鞭策?鑒於性道德淪喪的隱憂,我甚至力挽狂瀾般,為傳統的「貞節牌坊」作了「世說新語」──貞操不應限於兩性的性關係,它是每個人對自己尊嚴的維護,與對生活原則的堅持。現代化的貞操觀念,應從禮教的桎梏提升為人性的修鍊,從被動的束縛轉換為主動的操持,更從女性片面的倫理,擴展為兩性全面的道德戒律。
很久以前我讀過這樣的一段話:「一個新思想的產生是對當地社會最大的恭維,因為就像沒有一個股東會對即將破產的公司再作新的投資一樣,沒有一個對社會絕望的人願意致力於新觀念的倡導。」
無疑地,新女性主義,套用三民主義模式,它是:
一種思想──它順應時代潮流,也基於社會需要;
一種信仰──它主張兩性社會的繁榮與和諧應以男女的實質平等為基礎;
一種力量──它要消除傳統對女子的偏見,重建現代合理的價值觀念,以再造女子獨立自主的人格,並促進男女真平等社會的實現。
新女性主義在十多年前被有志一同的男女朋友們所倡導促進,無疑地,我們都對台灣社會懷抱相當的熱忱與信心,然而多年的閱歷使我相信另外的一段話:「一個不能用理性新看待新思想的人,必是社會進步的絆腳石。」
你我人人嚮往一個朝氣蓬勃、多元開放的社會,尼采不是說過麼?「痛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處在日形憂患之中的你我,豈有無病呻吟,對酒悲歌的權利!我你都不能是對人間世絕望的人,都還應該秉持一己的良知良能去己立立人,己達達人。
就是基於這個信念吧,李昂、向陽、魏淑貞、李元貞、宋澤萊以及楊國樞等先生女士,對於拙著《這三個女人》的發表和出書,先後給過難能可貴的掖助和期勉,他們的雲誼隆情,絕不止於對我這個咫尺天涯客劫後歸來的慰懷,毋寧是知識份子道德勇氣的表現,感佩之情,盡在不言中矣。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寫於尼爾森風雨交加時
原載於一九八五年自立晚報出版《這三個女人》
鐵窗下搖筆桿 呂秀蓮
人的記憶是很奇妙的東西,有點像百寶盒吧,打開來琳瑯滿目,闔起來就什麼也看不見了。我出獄才一個月,漫長的一九三三個坐牢日子,竟已被我壓得扁扁的,只剩下濃縮了的記憶。是我健忘麼?也許。下意識裡寧可汲取新鮮的、光明的歡愉,以營養我一度枯萎的生機。
此刻要追述獄中寫作的情形,我便只想捕捉那不帶感傷,不牽人愁恨的點滴。
我的鐵窗生涯,就空間言,先是在景美軍法處看守所四疊榻榻米的囚室裡,總共蟄居二百九十天,其後移監土城仁愛教育實驗所,二者都曾更換過住處。景美的易室而居,是由於押房四壁加裝保麗龍和閉路電視的緣故,到土城我們先住進仁教所副主任的值班室,不久又搬到國防部特別為陳菊跟我興建的一棟有小套房小院落的「別墅」裡去;「別墅」因有重重鐵門鐵柵而使我們免除治安日壞的恐懼,也因有閉路電視和竊聽設施而使我們倍感「身價不凡」。
坐牢的空間自由絕對有限,但時間自由的限制卻是相對的,就其支配權來說,我把它分作四個階段:
一、調查偵訊階段總共五十天,一切聽命調查人員,除接受偵訊外,不能看書,不能使用紙筆,也無從與人交談,時間上全無自由可言。
二、開庭審判移監土城前,共約二百天,時間很自由,可看書並用紙筆,但紙張的用量受嚴格管制,每天核對,不得短少,後來還可以跟陳菊、林文珍和張溫鷹交談。
三、十點熄燈階段,約四年。我們因被分界監禁,不參與仁教所活動,只受十點熄燈的限制和每週上課半天的安排,其餘時間自理。熄燈後我常就著室外水銀燈的微光寫作。
四、使用檯燈階段,由於我罹患慢性皮膚蕁痲疹,夜晚奇癢難眠,終獲准於熄燈後使用檯燈,時間的支配至此得到相當的自由,這是出獄前一年的事。
約略交代過獄中生活的時空座標後,請讓我告訴您,鐵窗下我是怎樣搖筆桿的?又搖了些什麼?
仁教所有桌有椅,寫作的物質條件還不錯,軍法處看守所卻大異其趣。吃喝拉屎洗漱全在囚室裡,窗戶是高高在上的,唯一與室外溝通的是一方十二乘三公分的眼孔,再就是牆腳下傳遞飯菜的「狗洞」,而眼孔經常要被外面的銅板給罩住,於是觸目所及,除了刺眼的黃色塑膠牆(為防撞壁自殺而設),便是高懸在天花板上東南西北四個角落的電眼裝置。囚室之內除馬桶蓋外,再沒有硬而平的東西,我腦子不靈光,未曾想到在馬桶上求靈感(有人如此),但運氣還不壞,一位好心的管理員為我弄來一塊紙板,我把它糊上白紙,倚著牆腳,墊著雙膝,就沒命地寫起來了。實在累極,我又想到把棉被毯子摺疊在一起,連人帶筆趴上去,趴得腰痠背疼,猶不願歇息。我那篇曾令法庭上下唏噓成一片的「最後陳述」,便是漏夜在棉被上一字一淚泣書而成的。
遺憾的是,在那樣艱困的環境與惡劣的心情下寫就的東西,除了法庭上宣讀的「最後陳述」外,其餘的──包括與軍法大審有關的文件和小說三篇──在移監土城時,全部被軍法處扣留。這一扣留,自自然然地摧毀了我在鐵窗下搖筆桿的全盤計畫,以至於有兩年半的時間,我不曾為自己動筆。
直到七十二年三月間,我方始獲得「自撰文稿經送檢後,於開釋時發還」的允諾,並將軍法處扣留的三篇小說稿索回。鐵窗下搖筆桿的念頭於焉復萌。
由於寫作環境與寫作心情的日漸改善,兩年來我以嚴肅的態度撰述較具學術性的論文,至於小說創作,也由粗淺的演練逐漸進入狀況,技巧可能未臻純熟,然而所欲表達的理念均經反覆思索,稿成之後也都與陳菊討論過。綜括這兩年筆耕的些許收穫,共四十萬多字,可分為三大類別:
一、法律類
1.夫妻財產制修訂芻議
2.美國憲法的言論自由權
二、哲學類
1.人權思想的哲學探討
2.儒家思想的人權觀
3.中國哲學的生命觀
4.宇宙、生命與人生
三、小說類
1.這個三個女人
2.貞節牌坊
3.小鎮餘暉
4.情
5.無眠之夜
6.拾穗
7.......
我宿習法律,卻不務正業久矣,當年在哈佛大學選修「婦女與法律」及「美國憲法」等課程,並撰寫〈墮胎合法化〉與〈夫妻財產制〉兩篇論文,返台後因投身政治,未暇將之迻譯成中文。今優生保健法已通過,而民法夫妻財產制的諸多迂陋仍未革除,乃將該稿譯成中文,他日或能供有司作再修訂之參考。
言論自由是民主政治的礎石,因其激勵並傳播思想,而思想引導行動,行動促成組織,沒有自由的言論,何來政治的民主?然而自由有其極限,在此極限內,言論(包括傳播、講學、著作、出版等)應受保障。言論自由的極限為何?它有其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原理,也不無因時地而制宜的必要,立國二百年的美國在言論自由方面有其源遠流長的歷史,其聯邦最高法院所作有關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判例,對於「言論自由」的實質內容與形式規定先後作了極為詳盡週妥的檢驗,鑑於國內涉及言論自由的爭端層出不窮,而政界、法界與輿論界對此又莫衷一是,無有定論,我遂著手整理有關的判例;「可惜」尚未完成,人已出獄。
人權是廿世紀政治思想的特色,它常被視為西方基督文明產物,實則不然。在我涉獵先秦哲學思想時,我欣悅地發現,詩書經以及孔孟學說中原本孕含著濃厚的人本──人權思想,可與西方的人權思想相映成趣。如果有人執持「人權」是舶來品的藉口而拒絕認同,當心他已犯了「數典忘祖」的罪過!
我在獄中寫就〈人權思想的哲學探討〉和〈儒家思想的人權觀〉等文章,據說曾使某些人不安了一陣,經我表示,我人在獄中而膽敢探討人權問題,其實是對有關當局的一項恭維後,他們一度同意將該二稿予以發表,又因故作罷。此一經過恰似有回我要求獄方准許家姊送入我自撰的〈墮胎合法化〉論文稿被拒一樣,饒富謬誤的趣味。墮胎合法化絕不等於鼓勵墮胎,探討人權思想,又怎能被無端目為攻訐政府呢?
對人權思想的探討引發了我對「人」本身的興趣,因此著手撰寫一本《人與人權》的書。我分別從科學與哲學的立場,去了解宇宙、生命和人生的問題,並思索三者之間的關係,而以中西方哲學對「生命」的看法,作為詮釋的樞紐,進而指出人生哲學的當代意義,亦即從大宇宙的創化,衍生出小宇宙的人,而人生在宇宙之中,以其特殊的結構和意義,展現出生命的目的,在於使人與天、人與人、人與物相互之間圓融合一。這本書由於內容深奧晦澀,而獄中寸步難行,資料極有限,寫了十多萬字,即告暫停,尚待來日的努力。
寫論說和小品文,是我習以為常的事,小說卻是心嚮往之而不曾嚐試的,我深知文學藝術特有的魅力,絕非硬梆梆的理論或直來直往的政治所能企及,而獄中有的是磨菇的時間,於是我也跟著邯鄲學步起來,只是難逃方家法眼,也是意料中事。
當初獲准寫作既以「送檢」為前提,我在構思時首先就得撇開一切敏感問題,因而決定以兩性之間的關係作為取材的對象,藉以呼應十年來我所倡導的「新女性主義」思想,而以《這三個女人》、〈拾穗〉、〈小鎮餘暉〉、〈貞節牌坊〉、《情》等篇差堪我意。
《情》寫的是親情、友情、愛情、物情與鄉情之間的糾葛和理析。小說人物以一個貧困家庭裡當過娼妓的姊姊,在工廠工作的妹妹和赴美攻讀博士學位的兄弟為主角,鄉間小市民、工廠員工及海外留學生與其洋朋友等為配角,不同的身分有其不同的語言和不同的思想,基本上我想表達的是──無情人生有情人。為著救濟弟弟的急病,姊姊被賣為娼,為著供應哥哥上學,妹妹自願去當女工,然後這個備受呵護的兄弟,長大而且即將功成名就了,他是繼續追求一己的理想而無視家人對他的呼喚呢,還是飲水思源,毅然放棄自己的前途回報他的姊妹?故事雖是李家的故事,涵攝的卻是台灣社會的縮影。全文十數萬字,將另行出書。
此外四稿皆屬短篇小說,其中〈貞節牌坊〉是就傳統貞操觀念所作的「世說新語」。我以為貞操不應限於兩性的性關係,它是每個人對自己尊嚴的維護,與對生活原則的堅持。現代化的貞操觀念,應從禮教的桎梏提升為人性的修鍊,從被動的束縛轉換為主動的操持,更從女性片面的倫理擴充為兩性全面的道德誡律。故事主角藍玉青原為富家千金,由於一場大火而家破人亡,為償父債並為養母弟,她淪為紅牌舞女,在面對豪門巨賈的銀彈攻勢下,她怎樣把持住自己?因為她背後有一位剛毅不俗的男孩在從旁激勵──女性在傳統的桎梏中掙扎解脫時,男士們,請擺出你們的紳士風度來助她一臂之力!
〈小鎮餘暉〉寫一個賣蚵煎的女兒與鎮上權貴之家所發生的情緣。那權貴之家留美的博士兒子娶了患有不治之疾的女子為妻,而且生下一女才黯然逝去。這段淒美的故事感動了賣蚵煎的女兒,經由魚雁往返,兩人建立起感情的橋梁,卻被權貴之家的門閥意識從中作梗,傷心之餘他閉著眼睛接受了父母安排的女孩,這女孩憎惡再婚的事實,於是前妻之女便被遙遙摒斥於他們再婚的門外,任由她在小鎮的老家自生自滅。故事開端於賣蚵煎的女兒隨夫調職回到小鎮來,並擔任鎮上的國中教師,而驚覺到那可憐的前妻之女適是她班上的學生。隨著師生情誼的推展,我探討起世俗的門閥之見,與西風東漸後的人倫關係,而隱藏在門閥之見與倫理關係背面的是,一位外表拙樸,心性卻寬厚篤實的好丈夫,這個放牛出身的好丈夫,在做人的情操方面絲毫不亞於權貴出身的太空博士──算是我對「新男性」的側寫吧!
〈拾穗〉屬於一個自信、自愛而且自苦的女孩的心靈剖白。這個被男友譏刺為冷血動物的奇特女孩,在男友的婚禮上,赫然從他的眼光中讀出太多的悱惻和怨艾。抽出被新郎緊握不放的手,拋下給新娘一句隨俗的恭喜,她匆匆逃離會場,獨自漫步在夏日晚間的人行道上,為自己居然做了一名感情的劊子手而惴惴難安──而自我解析。她發現自己既心儀於一種可以使她發光發熱,如醉如痴的戀情,又害怕被狂熱焚毀,因情愛沉溺,這矛盾的心理使她雖願為心之所愛作精神守寡,卻雅不願隨波逐流,墜入婚姻的流俗,在服膺「情字不可錯過,緣字不可強求」的傳統諺語之餘,她也怵然於蘇格拉底得意門徒空手而回的拾穗警惕。
《這三個女人》是最徹底闡揚「新女性主義」思想的小說。如果有人視之為「非小說」,我也不反對,因為其中敘述了太多的道理,我幾度考慮予以剔除,又覺得已許久不曾就婦女問題大發議論了,何不將它存留,好就教於高明?
文中的「三個女人」是三位極要好的大學女同學,她們的性向和際遇各別,自然畢業以後,每個人的人生旅程各有千秋。許玉芝原是大學講師,婚後隨夫赴美,全心全意做賢妻良母,擁有博士丈夫,二男一女和花園洋房;高秀如身任大學系主任,能幹豁達而未婚,又兼具古道心腸,是位熱誠的社會工作者;汪雲這個麗質天生的美人和她相戀多年的白馬王子結成眷屬後,一味沉湎於少奶奶的舒泰生活,直到有一天她發現丈夫移情別戀,而且車禍喪生,她才如夢乍醒。
故事分作三段進行。之一的〈有朋自遠方來〉,以某個夏日午後舊金山郊區為舞台,許玉芝為招待老友高秀如的到來而大忙特忙,內心裡尤其七上八下翻騰不已。通過許玉芝的忙碌,我們看出旅居海外的家庭主婦其生活內容之貧與煩,再通過許玉芝對高秀如的稱羡,我們發現表面上擁有一切的女人其實正因失落了自我而大起恐慌。然則恐慌之後呢?逃避再湮滅自己,抑或勇敢地破殼而出?
之二的〈今夕何夕〉以翌年某個夏日的週末晚上為定點,描寫高秀如單身但不單調的生活。當許玉芝的整個下午都離不開瑣瑣屑屑的家務事,高秀如的短暫夜晚,卻是充實而且多采多姿,因為她豐沛的心靈包容著世間許許多多的人與事。異性的愛情,相對地,便不會是她生命的全部了。然而,她又是個血性女子,一張海報圖,一陣電話鈴響,一碗酸辣麵,依然要翕動她的心田深處。
之三的〈回首〉,寫守寡三年的汪雲對亡夫的愛恨和對往事前塵的自省,時間定點是第三個夏末的早晨,她打發好雙胞胎女兒上學後,獨個兒邁向自己經營的服飾店,一步一回首,想及她跟丈夫的往日情懷,她對幸福和美麗的錯誤觀念,還有丈夫外遇的謎題。驀然地,她發現她原來擁有的竟是一樁荒謬而慚愧的婚姻,她愛丈夫,卻愛得迷糊,而另外一個女人,愛得不比她少,而且比她辛苦。謎底揭曉了,她如何面對她所嫉恨的女人?
當然,以上不過簡單鉤勒出《這三個女人》的梗概,做為女性知識份子,她們的業力因緣在現代社會生活中,必然會產生許多激變,這是本文所試圖探討的。從傳統到現在,再通往未來,這條亙古綿延的人生道路,是生生不息,日新月異的,女性同胞豈可抱殘守缺?而她們所摯愛的男士們,非但不能相應不理,尤其應該加以勉勵和提攜。
於此,尚須提請讀者注意的是,我以下午、夜晚和早晨作為三篇小說的時間定點,是別有寓意的。許玉芝擁有世俗豔羨的一切幸福,像午後在一天當中所代表的盛況,只是下午過了便是黃昏,擁抱婚姻而失卻自我的女人,別忘了「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警語!汪雲從迷糊的愛情中甦醒,從守寡的哀傷中復活,更從對別人的怨懟中自省,雖然她失去了許多,她所抖落的正是阻礙她重生的絆腳石,她的生命,其實仍如一天當中的早晨,又長又充滿希望!至於高秀如這樣的女人,己立而立人,小我之外另有大我的生命,即使在夜晚,也難掩其滿天星斗般的光華。
最後略述本文寫作的過程,這篇全長六萬多字的小說,始於六十九年五月間,軍法大審結束,十二年判刑定讞之後,剛獲准使用紙筆時,心境與環境的惡劣可想而知,當時只寫好〈有朋自遠方來〉,用的十行紙,自然是趴在棉被上面完成的。三年之後的七十二年九月十一日上午,我因專注於看書,眼睛極感不適,順手抓來眼藥水往左眼一點,頓覺鉅痛無比,淚下如雨,原來我胡亂間點下的是用眼藥瓶改裝的明星花露水(有止癢效用),酒精成分極高,差點沒把我眼角膜燒壞掉。經過一陣沖洗,下午三時許獲准到外就醫,眼科大夫於是把我的雙眼統統包紮住,我因此充當兩日夜的瞎子。平日忙碌慣了,我即使坐牢也坐得分秒必爭,忽然間靈魂之窗被罩上幃幕,一切便都百無聊賴起來,忍無可忍之下,我首先想到摸索著繡花,繡了一半,因常要陳菊幫我穿針線太麻煩,索興躺在床舖上構思小說,〈今夕何夕〉就是這兩天眼盲心不盲所打點的腹稿。
至於末篇〈回首〉,則是為追念先慈逝世三週年而作。母親生前對我有異於常人的呵護,因驟聞愛女罹案被捕而踉蹌倒地,終至骨折中風,臥床不起,病榻間不時以淚洗面,並頻呼吾名,如此幾達兩年之久,終於含恨西去。而我身繫囹圄,咫尺天涯,除面壁自愆,絕食請願外,紿終未曾獲晤一面。即連病故之後,法定廿四小時的喪假亦被限制在午夜十一至一時之間奔喪,我因其太傷風敗俗而拒絕,不得已乃於翌日祭禮時分在院外當天長跪不起,幾至昏厥。從此母女幽冥兩隔,相見永無期,每思及此,不覺慟徹肺腑,難以自已。清明那日,我撐病軀登臨墓地,但見黃土一坯,而慈母安在哉?放眼青山白雲間,念天地悠悠,而人間無情有若此者,愴然淚下之餘,唯有憮喟地老天荒不了情!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返家滿月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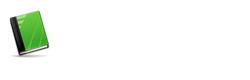

















![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係【原著劇本|上冊】:★隨書贈禮[繪本卡組]: 8款原版繪本卡X經典對白X精緻信封袋](https://www.books.com.tw/image/getImage?i=https%3A%2F%2Fwww.books.com.tw%2Fimg%2F001%2F087%2F40%2F0010874079.jpg&width=125&height=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