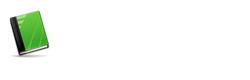自序
濃郁的思念
縱然放棄悲傷的沙袋或許能讓快樂的熱氣球上升,
但同時,也意味著將與過去的某部分從此分離。
我希望能盡力地保留住各段瑣碎的、關於爸爸的記憶剪影,
管他什麼口味、什麼形狀,都能持續地停留在我的心中……
我要說的是,人生乃一道由各種情感交錯堆疊而成的千層麵。
原料來自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朋友,情侶,或是家人;相逢,相守,或是相別。
千萬種選項形成億萬個組合,如同各套食譜。
然而其中那些化作回憶,觸碰到心弦的感受卻是不變的。
我想起了寫這本書前的某天下午,整理物品時,在爸爸櫃子裡找到一個牛皮紙袋,裡面放了一幅我國小的美術作業。那是用蠟筆來回塗出,一棟拙劣的尖頂磚瓦房子,身形巨大的父母站在房子前,中間牽著我們幾個小孩子。手拉手的一家人像是倒放的糖葫蘆,臉上都掛著兩團黑溜溜的眼睛跟一張半圓形的嘴巴。
當初畫好後隨手一扔,卻被爸爸珍藏起來,一直到了今日。
那個紙袋裡還有許多類似的畫,或是每年爸爸生日,我們做的手繪卡片。一張張對摺的卡紙,正面下緣剪出一道可以打開的門,裡面寫著歪曲的——
「爸爸,生日ㄎㄨㄞ□樂。」
我怔怔地看著自己小時候的作品,出了神。
畢卡索也不會像我一樣這麼耽溺於自己童年的藝術天賦吧。
當然,才不是因為畫本身。我是望向那藏在混亂筆跡中的時光鏡子,它倒映出十幾年前年輕的爸爸,帶著微笑欣賞這些作品的表情。
聽過「銘印現象」嗎?
小鴨在出生後會將第一眼看到的生物當作母親。
某人鐵定誤解了這個理論,以為是要讓小鴨持續地看到自己的爸媽,牠們才不會轉頭就跟一條狗跑了。就這樣,爸爸比跟蹤狂還要亦步亦趨地陪伴在我們身邊。
冬天,他寬大粗糙的手像暖暖包一樣熱呼呼的。
夏天,當我吐著舌頭喊熱時,他會破第一萬次例,帶我去吃冰。
「不可以跟你媽說喔。」
儘管銘印現象的有效期限早過了,但這樣天天集訓般相處,讓父子間的故事像梅雨季的水壩,蓄滿了一整個山谷。水氣蒸發後凝聚在上方,化作摸不著,卻感受得到的溫熱親情。
那時候的我還很小,興致來了還可以坐上爸爸的肩膀。
現在的我比爸爸還高一點,而他人呢?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兒時光陰緬懷起來總是特別美好的。反之,與爸爸分離的最後一個月,迄今回想依然會有一股嘔吐的衝動,想將所有傷痛從受創的靈魂深處全部釋放。
晴天霹靂接獲了爸爸罹患肺腺癌末期的噩耗,從德國趕回台灣時,爸爸依然提起精神到機場迎接我。他說是為了讓我放心,他說他根本沒有感覺那麼嚴重,他甚至問我請假幾天,可別耽擱了學業。
我才不理會這種分不清輕重緩急的提醒呢。
最後,說來諷刺,的確沒有耽擱到什麼學業,因為才短短的一個半月,原本還在家裡爽朗笑著的爸爸,已經在加護病房,沒有跟大家道聲晚安便沉沉地睡去了。
那是那陣子以來他睡得最長、最安穩的一覺。
很多長輩說這樣的離去其實是幸福的,因為爸爸沒有遭受太多的痛苦。
「只是苦了留下來的家人沒有做好準備,捨不得啊。」
迄今我還是無法完全接受這近似寬慰的說法,這需要累積一定人生智慧後才能豁達領悟的說法。但至少我學到,很多事情不管你接受不接受,它都會發生。
就像看似幸福的人生,原來竟然如此脆弱,可以像軟化的冰淇淋,隨便一挖就出現個大窟窿。
很多問題,它也不像工程領域中存在所謂的最佳解,有時候,它甚至無解。
回到德國,不知情的房東關心地問爸爸的狀況好點沒,正當我聳聳肩,講出早已準備好的台詞:
「At least, he is not suffering anymore.」(至少,他現在不會再受苦了。)
眼淚忽然無可抑制地順著臉頰往下流。那是父子親情,凝聚而成的水珠。
人的一生得到很多,但最終都將陸續化成無奈,消失在虛空當中。
只留下腦袋瓜子裡的那盤千層麵。
據說人腦內有一種機制,會讓痛苦的回憶像皮膚上的傷口一樣逐漸封閉癒合,只留下一條淡粉紅色的疤痕,而那多餘的空間,就讓快樂的記憶像氣球似地充大,滿溢在整個大腦之中。
如果不這樣,那許多人終將抱著鉛塊般的沉重往事度過餘生了。
真不愧是萬物之靈,連無法控制的部分都那麼聰明體貼。
但目前我還不想這樣,縱然放棄悲傷的沙袋或許能讓快樂的熱氣球上升,但同時,也意味著將與過去的某部分從此分離。
我希望能盡力地保留住各段瑣碎的、關於爸爸的記憶剪影,管他什麼口味、什麼形狀,都能持續地停留在我的心中,像一甕女兒紅放在某個角落釀著,偶爾過去掀開,深深吸一口氣,可能被嗆到咳嗽直冒眼淚,也可能嘴角上揚地細細品嚐。
於是我將與爸爸二十七年來短暫有如白駒過隙的相處時光,挑出腦海中閃過的二十八個有笑有淚的片段,放進烤箱內焗烤。
叮的一聲響起。
濃稠的起士如同我們父子無法分離的情感,金黃色的表皮透露著我對父親的景仰,而那股充斥在整間房裡的香味,那份思念──
我打開窗戶,希望能讓它飄到更遠的天邊,讓父親也能聞到。
賴以威
前言
最後一場演講
退休後,老爸就過著在家寫字典的日子;沒過幾年,又一頭栽進趣味數學的領域。
「誰說追逐理想是你們年輕人的權利,老頭子也可以啊。」爸爸笑著說。
多年來,老爸的身教就像螢光筆,在我心中一再畫下每項該注意的重點。
也彷彿像他所說的—「我只給釣竿。」
老爸離開了。
我們畢竟不是活在童話故事裡,這世界沒有那麼多的奇蹟。
話說回來,與老爸一起生活的這二十七年,就已經是我一輩子難以忘懷的奇蹟與回憶了。
可惜的是,最後這幾年,我因為學業的關係長期在德國生活,沒有辦法像以前一樣和老爸朝夕相處,只能透過網路,互相加油。
為我的學業,以及老爸的夢想加油。
因為懷抱著編撰字典的夢想,老爸在國小教書一滿二十五年就退休,過著在家寫字典的日子。從小看到大視為理所當然的事,現在一想,倒不清楚老爸是怎麼開始的。似乎是某次受委託修訂教材時,發現同一個字在不同字典裡竟有截然相異的解釋,總是喜歡追根究柢的老爸,就這樣鑽研起來了。
沒過幾年,負責籌辦台北市立新生國小的老同事,邀請原本教自然科學的老爸幫忙設計理科教學環境,對教育仍懷有熱忱的他,因此蒐集了一大疊數學遊戲,又一頭栽進了趣味數學的研究領域。
從新生國小開始,協助郭台強先生成立「永真教育基金會」,一步步地擴展到在台中科博館與台北科教館等地舉辦研習活動,後來甚至還代表台灣去參加兩岸三地數學論壇。每次聊起這個話題,我都可以看見老爸的眼神中散發出光彩:
「誰說追逐理想是你們年輕人的權利,老頭子也可以啊。」爸爸笑著說。
二○○八年,《聯合報》刊登了一篇老爸推廣趣味數學的報導,引起一些學校、老師的興趣和注意,加上先前舉辦研習營時發現教育資源嚴重分配不均,老爸開始思考:
「能讓一位老師知道我的理念,就等於讓至少一整個班級的學生受惠。比起教一個學生,當然效果要大多了。」
「但那只是理想狀況,很多孩子現在就需要,哪能等你去把老師召集過來,讓老師慢慢學,再教學生呢?」
因為想要照顧到更多孩子,尤其是屬於弱勢的偏遠地區,老爸展開了下鄉之旅。一整年下來除了花東還來不及造訪,幾乎各縣市都有他去演講過的蹤跡。但或許是太操勞了,二○○九年七月初在東門國小演講完之後,當晚他就因身體不適被送進了急診室。經過兩天的診斷,判定是肺腺癌末期。
一接獲這個消息,我立刻請了長假從德國趕回台灣。
「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
國中時像嚼橡膠一樣硬吞下的古文,如今卻像咒語般在腦中盤旋不去。儘管,視訊裡的老爸看起來神采依舊,但任誰都明白癌症末期的嚴重性。
我一直以為死亡距離很遙遠,至少不可能發生在周圍的人身上。誰知道它就這樣大剌剌地光天化日下闖進來,忽然間,橫眉冷眼的站在我們面前。
然而,我猜老爸一定讓它也不禁納悶:
「這傢伙怎麼還不好好養病來對付我,成天跑來跑去?」
在我上飛機前的最後一次視訊通話,老爸笑笑地說:
「等我把數學和字典這兩件事情稍微處理一下,有著落了我再開始認真治病。」
真是皇帝不急,急死太監。我了解到,自己回去的目的不單是陪在老爸身旁,更要拉著他專心養病,別再四處奔波了。
只是,就像屬虎的爸爸常常虧我這屬狗的兒子:
「虎父無犬子,怎麼剛好就這麼巧呢?」
犬子終究是拉不住虎父的。到後來反而是我被老爸帶著,到處奔走做最後的理念推廣,並尋找能託付數學與字典理想的老師。
老爸最後一場演講那天的景象,到如今都還歷歷在目。
※※※
我很生氣地看著前方,縮在椅子上咳到臉紅的老爸,頸部的青筋猙獰地浮現。那拿著衛生紙捂嘴的右手臂上繞了一圈白色繃帶,是剛剛打完顯影劑後綁上的。
我們在亞東醫院剛做完電腦斷層檢查,下午要去附近的中山國中對台北縣數學輔導團演講。
一場在剛知道生病的隔天,老爸立刻跑去台北縣教育局推銷自己的教學理念所換來的演講。
那天他接連跑了台北縣教育局及教育部,反倒是原本要去的台大醫院因此取消了。老爸一向強韌的意志力此刻卻不斷損耗著他的身體,這樣矛盾的劇本在我眼前上演了快一個月,我的負面情緒像吹氣球一樣每每漲大,旋即又因心疼他的虛弱而消退。
然而,從老爸昨天臨時被告知演講排在今天下午,而他又爽快答應之後,我感覺自己已經逼近臨界點了。
為什麼不肯好好養病,反而在生病之後把行程排得更滿呢?這根本是本末倒置。
中午一點多,我跟老爸還有叔叔在中山國中的一間教室休息。三個人蜷著腳縮在課桌椅裡午睡,電風扇旋轉發出的聲響和蟬鳴反襯出夏日午後的寧靜。我想起半小時前,我們還在爭論要不要先打電話給輔導團的主任。
「約好是下午兩點,就不要給人家添麻煩,提早那麼多到。我們在醫院大廳休息就好了。」
「醫院這麼不乾淨,你如果感染了怎麼辦?醫生可是強調過千萬不可以感染的。早點過去又不會怎樣,哪有差啊!」
都到這種關頭了,還要在意會麻煩別人的小事,我感覺到腦袋裡的水閘被打開,對老爸的不滿一股腦地宣洩了出來。
咚!突然踩空的感覺讓我從睡夢中驚醒。沿著橫越過手臂的視線,我看到老爸低頭皺眉坐著,雙手慢慢地撫摸著膝蓋。
「……不舒服嗎?」
剛吵完架,我的關心中帶著點生澀。
「各位老師、前輩大家好。」
麥克風放大了老爸的音量,以及他的虛弱。
相似的場合,已是兩週來第四次了。前次到教育部報告時,老爸還不需要麥克風,不會用雷射筆的他也還有精力在屏幕前走來走去。那次中央輔導團的老師們很感動,紛紛提出建議。
「我下個月在三峽全國教師研習營有個演講機會,不如讓給賴老師吧。」
「我們可以招募有興趣參與的老師,直接在賴老師家附近辦個小型研習營好了。」
老爸笑得很開心,不斷提醒我抄下老師們的聯絡方式。行事曆滿滿記著從八月十一日開始,平均每週兩場演講的高密度行程,我不禁擔憂起他的身體能否負荷得了。
問題是擔心也沒用。老爸說我們家每個小孩都很固執、有自己的意見。我倒覺得,把我們的固執整個加總起來,差不多才是老爸的程度吧。
我下意識地環視教室。約莫十幾位老師來參加,還有一兩個小孩。放眼望去,有位老師就像大學生上必修演講課時一樣,低著頭在用筆電。
我轉頭望向老爸。他一定看到了,卻毫不在意,依然笑嘻嘻地賣力演出。
我又想起前幾次的演講或訪談,儘管大家都很樂意幫忙,但那樣的善意下卻像隱藏著一堵溫柔的牆,讓老爸碰了一鼻子灰。
「賴老師的教法很適合資優班學生,或是辦趣味數學營隊。」
(「賴老師的教法對於一般學生是否適用,還有待評估。」)
「我們可以替賴老師辦研習營。」
(「我們現在也只能替賴老師辦研習營,不可能全面性地將這套方法透過正式管道直接引進學校。」)
這不是誰的錯,沒有人能在短期內改變教育方針,這點跑過很多學校的老爸比誰都清楚。有一兩次,我甚至因為拜訪的教授或老師表明無能為力時,暗自開心——
或許這樣,老爸就會放棄這個不切實際的想法,好好養病了。
我邊看老爸有點受傷的側臉邊偷偷想著。只見他抽動嘴角苦笑了一下:「教授說得沒錯,我知道這是螞蟻撼樹、愚公移山。不過,總得有人當第一個愚公吧。」
我真是低估他的固執了。
那麼,我又為何會這樣放任他繼續在台上講話呢?眼看咳嗽的時間都快超過說話的份量了。
屏幕上出現了「貓捉老鼠」單元,這個遊戲當初我也是先玩輸了老爸一次,才知道原理的。「博士生也不過爾爾嘛。」
那時老爸很得意地羞辱我。
果然,一陣陣「咦,真的耶!」的聲音從台下冒了出來。
老爸像用惡作劇騙倒一堆人的小孩子,促狹地在旁邊笑著,示意大家先想想看,再公布原理。那時候我忽然了解——
有一部分的我,只是自私地喜歡老爸在台上開心笑著的表情,想看到他和沒生病之前一樣開朗的笑容,才陪著他繼續出來演講的。
演講到一半,終於承受不住一早就開始的奔走,再變了兩個繩結魔術後,爸爸向老師們連番道歉,坐下來休息了。
輔導團的一位老師熱心地想著推廣方法:「賴老師有沒有考慮過把趣味遊戲直接和課程結合,然後編寫教材?這是最快最有效的,可以讓第一線的老師立刻就用到。」
已經坐著在喘氣的老爸,聽到了又忍不住站起來回應。
「謝謝老師的建議,我也知道這是最快的方法。但我怕這樣做,老師們會因為有了教材,反而扼殺了自己創新的空間。」
「趣味數學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創意。我擔心光編教材無法讓老師們體會我的想法,反而只是照本宣科教孩子。這樣老師自己沒有得到創意,學生又怎麼會被激發創意呢?所以我才想這樣面對面地討論……」
「我們說不要給孩子魚吃,要給他們釣竿。這套趣味數學的教法不是更該如此嗎?我們也只能給老師們釣……」
不知道為什麼,說到「竿」這個字的時候,老爸忽然像電視被消音一樣發不出聲。所有的人,連老爸自己都愣住了。他吸了口氣重新說話,卻依然只見嘴巴動了一下。
在場的老師,或許不一定認同這樣近乎唐吉軻德式的理念,但是在當下,所有人都全神貫注望著老爸,等他把話說完……
老爸搖搖頭苦笑著:「奇怪,為什麼這個字講不出來。」
應該是這個字最需要用肺部施力吧。
他又用力吸了一口氣——「釣竿。」
看著老爸總算把話講完,鬆了一口氣露出笑容,那表情就像根針,把我心裡那顆憤怒的氣球徹底洩掉,只留下不捨與無奈。
※※※
晚上十點多,爸爸房間持續傳來的咳嗽聲忽然停止了好一會兒。我走過去探看,只見他低著頭盤腿坐在地上,跟今天中午在教室裡一樣,蹙著眉心,嘴角不自覺地下彎。生病後獨自一個人時,爸爸總會露出這個表情。
「在想什麼呢?」
我坐到他身旁,順著脊椎骨往下按摩他的背。
「錯了,今天下午講太多了。我那樣強勢地主張自己的意見,會引人反感的。」
「你看你又來了,都什麼時候了,還那麼在意別人的感受。不會啦,那些老師才不會因為這樣就不高興。」
我笑著回他,稍微加強力道,拍了幾下他的背。
爸爸沒有說話。
要適時地站在別人的立場思考,這是小時候爸爸告訴過我的一項做人處世之道。他教導我的道理,絕對是自己也身體力行的。這樣的身教彷彿像螢光筆一樣,在我心中一再地畫下每項該注意的重點。
也彷彿像他所說的——
「我只給釣竿。」
幾天後,爸爸便因為身體無法負荷,取消原本安排好的行程緊急住院了。
第一天晚上,我們在急診室度過,看著他因為戴上氧氣罩總算能好好入眠,我心裡不禁想著——
爸爸其實沒有生病,他的意志比什麼時候都還要硬朗。
小時候我們很希望趕快長大,因為長大了就有能力去做更多事情。等到長大後才發現,就算真成了能摘下月亮的超級大人,也沒辦法再回到過去了。
幸好,我們還有回憶,它像台快門壞掉的傻瓜相機,任性地拍下各個生活片段,讓我們這些無法回頭的成人,可以在夜深人靜時拿出來,在月光下獨自把玩。
我闔上雙眼,腦海裡浮現了那個當年才到爸爸胸口高的我,以及總是爽朗地笑著,動不動就愛趁機講道理又愛開玩笑的爸爸。
我們兩個坐在客廳的沙發上閒聊著……
兒時的平淡生活原來竟是如此溫暖耀眼,刺得此刻在病床旁的我睜不開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