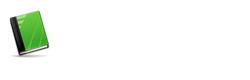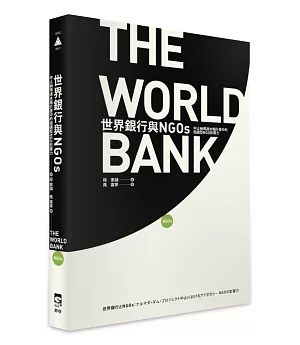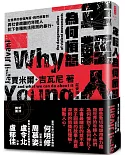作者序
本書為2006年於日本出版的《世界銀行與NGOs》中文版,是對總部位於美國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 C.)的國際組織「世界銀行」,自1980年代中期至1993年,因各國政府及倡議型NGO反對而終止印度納瑪達水壩計畫(Narmada Dam
Project)的相關研究。本書運用計畫過程中大量的世界銀行內部文書,印度與歐美的新聞報導,以及NGO資料,來闡釋終止過程的前因後果。此外,本書也以世界銀行總裁、理事會與事務局等內部組織的回應為基礎資料,說明倡議型NGO如何影響世界銀行已定案的計畫。
本書對於日本或現今的臺灣,大致可歸納出下列幾點助益。對於島國日本而言,國際合作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由於憲法等限制,日本對外的軍事援助受到限制,因此對日本政府而言,ODA(政府開發援助)成為確保國家利益的重要外交途徑。1980年代後半,日本受泡沫經濟影響,ODA除了使貿易所得的利潤,回饋給與日本貿易順差的開發中國家,同時也成為讓日本的一般公司、建設公司和顧問公司等能確實獲得利益的手段。在此過程中,許多計畫成為對開發中國家政府與官僚進行的各式各樣利益輸送或賄賂,使ODA成為媒體、各大報社、雜誌、研究者以及NGO批判的對象,質疑ODA究竟是「為了援助誰」而推動。
日本政府和外務省一方面接受上述批判,另一方面則運用評論以及為政府辯護的學者(也就是所謂的「御用學者」),反駁針對ODA的批評。這些人就是當時ODA論戰中,廣為人知的關係者和研究者。ODA論戰從1991年開始,直到1993年外務省停止對納瑪達水壩計畫的補助且完全失去提出反論的證據為止,在數家雜誌及學會中持續不斷辯論了三年。此後,NGO與學者針對印度的辛格勞利(Singrauli)等其他計畫,廣泛批判ODA,並同時對外務省和御用學者們提出反論。然而,外務省運用許多方式,試圖封殺對ODA的批判,而且肯定ODA的研究者與NGO人員,一再聘任他們擔任外務省與財務省相關的外部評價委員或審議委員。
和日本國內的行動不同,國際上將終止納瑪達水壩計畫,視為世界銀行的重大失敗,還出現「納瑪達的教訓」(the Narmada
Lesson)一詞。1993年3月底,印度政府申明婉拒世界銀行對納瑪達水壩計畫的相關貸款,從此世界銀行的納瑪達問題,轉變為世界銀行邁向改革的問題。也就是納瑪達問題導致世界銀行設立資訊公開制度,並且設置獨立調查的專家小組。促成改革的背後原因,是世界銀行第一出資國美國政府,以及站在承認世界銀行立場的美國議會,對此問題的深切關心。美國議會多次召開公聽會,討論世界銀行和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問題,而對於改革的關心,在1995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設立五十週年達到頂點—世界各國市民社會激發起討論,檢討支配世界經濟金融秩序的先進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IMF與世界銀行)的功能,更不用說在這些行動背後,存在著開發中國家與第三世界,對美國以及支持世界銀行的其他新先進國家的批評。美國與世界銀行的關係,在於歷任的世界銀行總裁都由美國人擔任。向來是國際組織的世界銀行,會被說成為了美國而存在的國際機構,原因不只是它的總部靠近華盛頓特區的白宮。
世界銀行終止對納瑪達水壩計畫融資這件事情,是透過NGO倡議的行動方針而達成,對於持續致力於從外部改革世界銀行與IMF體制的歐美NGO而言,可說是最初的重要成果之一。1990年代時,要求世界銀行與IMF負起責任的NGO團體所出版的研究書籍中,納瑪達水壩計畫是極為重要的案例。此外,在印度國內,其他水庫計畫仍由政府提供資金繼續進行。直到近年,印度的NGO組織「納瑪達自救會」(NBA)仍持續非暴力主義的抗爭運動。
另一方面,日本泡沫經濟崩壞,進入「失落的十年」。NGO也歷經世代交替。與納瑪達水庫問題有關的人員,或知曉納瑪達水庫問題發展過程的人員,從第一線退下。到了2000年以降,日本現職的NGO,幾乎已沒多少人還記得當初納瑪達問題時,是如何對世銀緊迫盯人、窮追猛打。取而代之、隨處可見的,是跟隨日本政府代表團一同參與「里約+10」(2002在南非召開的國際會議。是繼1992年在里約熱內盧召開聯合國環境開發高峰會「地球高峰會」之後,於十年後再度召開的會議),但在會議中沒立下顯著成果便敗下陣來的NGO;以及在外務省、國際合作銀行與財務省的三方會談中,作為代表而參與其中,卻操弄著一般人難以理解的專門用語的NGO,或是憑藉著從國外NGO取得獨家情報而活躍於會談的新興NGO。同時,世界銀行與亞洲開發銀行、日本政府、ODA等,仍持續進入開發中國家進行支援開發計畫,就結果來說並沒有停止援助的現象。大致看來,這一連串的現象,可說是日本外務省將NGO收編進政府的戰術,成功發揮效用。
循著上述的脈絡,本書透過納瑪達計畫的終止過程,以及闡釋世界銀行的意向決定結構,希望有助於NGO行動者、研究者以及一般大眾理解問題,並學習了解世界銀行與NGO過去的相關歷史,最重要的是希望今後不要發生相同的事件,並重蹈開發造成的暴力和悲劇的覆轍。東京的NGO(JASAES)員工在2001年對我說:「我們不會像段老師一樣汲取過去的事例」。對於日夜努力攝取新課題的二十幾歲年輕人來說(當時),我進行的研究想必被認為盡是些過去的老東西吧!不過,就像「歷史是會循環的」這句話所示,我們在與巨大權力與體制永無止境對峙的同時,學習過去的經驗十分重要。
之後又過了十四年,日本進入了「失落的二十年」,在這之間經歷多次首相交替(1999年起有小渕、青木〔臨時〕、森、小泉、安倍、福田、麻生、鳩山、菅、野田、安倍),以及一次自民黨與民主黨的政權交替,還有東日本大震災與福島第一原發事故。在景氣低迷下,日本社會的所得差距更明顯,拜金的資本主義漸形強大。
NGO也無法僅以理想主義進行活動。從世界銀行或日本ODA取得資金的NGO也紛紛成立。這些親政府的「御用NGO」,不但沒有批判體制的精神,反而利用世界銀行等組織的名聲,企圖壯大自己。而新興宗教團體成立的NGO,更讓這一切加速進行。他們表面上提倡解決貧困問題、援助開發中國家,實際上卻與其真實目的不符。在NGO的外表下,隱藏其真實身分,進行宣教活動,剝奪想認真參加國際合作工作的年輕人的意志與未來,這是必須正視的問題。在這個渾沌的狀況下,巨大的世界銀行組織仍不間斷地融資給開發中國家,同時使用CSO(市民社會組織)一詞,選擇其認為合適的NGO進行合作。每年秋天舉辦的IMF.世界銀行年會中,這些CSO會得到正式的認可參加。
世界銀行與臺灣的關係
1970年代,中國奪得聯合國代表權,中華民國(臺灣)退出聯合國。對於退出聯合國的臺灣而言,由聯合國、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所代表的國際社會,被視為遙遠的存在。不過在今日,在世界經濟或對中國投資的情況中,都不應過於小看臺灣的經濟功能。此外,臺灣領先其他華人社會的民主主義,以及以太陽花學運為代表,針對政治和社會問題,果決勇敢採取行動的年輕人,還有支持民主與學運的臺灣社會,讓沉溺在日常消費生活中的日本與歐美先進國家市民,得以重新關心政治,並回想起他們早已忘記卻十分重要的價值觀。若臺灣與臺灣人對「民族自決原則」有深切期盼,則國際社會在未來應該會認真面對並思考臺灣的國際地位。為了迎接這個時刻,學生與研究者,甚至新聞媒體等,都必須理解國際合作與國際機構的本質。
我與臺灣
我是清朝末年移居日本橫濱的華僑後裔,我的母親則出生於臺灣,在太平洋戰爭前,還在年幼時期便移居日本。1970年出生的我,從幼年到少年時期都住在橫濱的中華街,從父親那兒聽了許多關於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惡狀。此外,我小學時就讀孫文所創立的橫濱中華學院國小部,當時採用的是臺灣國立編譯館的教科書,我對國民黨推行的反共教育和軍國教育思想感到十分嫌惡。一方面身處於日本,與大多數「純粹的」日本人在不同的歷史背景與社會中出生成長,所以我能夠將中國、臺灣與日本三者相對化,並學習於在三者當中,以中立的視角看待事物。也就是不偏向任何一邊,或者不屬於任何一邊。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國人,亦非臺灣人,雖然一直有種源由於模糊歸屬意識而生的孤獨感伴隨著我,但這也成為我在追求學問的路途上,獲得真正獨創性的重要機會。我之所以選擇國際關係論與國際合作論為研究主題領域,以「NGO不信任國家」此假設作為研究準則,並且成為橫濱華人當中第一位大學教授,這一切我想與前述背景有深刻的關係。
因為厭惡國民黨推行的洗腦式愛國教育與反共教育,在橫濱中華學院小學部畢業後,就報考進入日本的國中與高中就讀。離開了由血緣與錢脈連結的華僑社會,也遠離了中華街。但也沒有接近共產黨獨裁下的中國。進入大學後,我選擇的研究主題是日本的ODA與NGO,因為想拉開自己與中國和臺灣的距離,希冀一邊觀察兩邊民主社會發展的陰暗面,一邊弄清楚兩者的發展,當時正是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的1989年到1993年。從不定期回臺灣故里的母親口中聽說,從飛機的窗戶往下看,可以看到流入河川的廢水,如此敘述讓我印象深刻。當時臺灣也在進行反公害運動,以及更進一步的環境保護運動,我相信一定有以此為目標孕育而生的市民團體和國際性NGO。1990年代,臺灣解除戒嚴數年後,由李登輝執政。不過,從過去的歷史發展來看,已無法天真地相信「民主化」的口號。隨後,我進入研究所取得碩士和博士的學位,直到我於大阪的大學任教,一直都專注於研究課題而尚未開始關注臺灣發展,當我第一次踏上臺灣的土地,已經是2008年3月、三十七歲那年。當時正值臺灣總統選舉期間。
至今又經過了六年,期間再度重習中文與臺灣的歷史、政治與社會狀況。為進行臺灣加入聯合國的研究,2010年4月開始在臺灣的國立成功大學,以訪問學者的身分進行一年的研究,並有機會在臺南生活。臺南與臺北路上往來的大群機車陣中,混雜著賓士與BMW,臺中的高速公路和市街上則有疾馳的藍寶堅尼和法拉利,這和1990年代的日本頗為相似。究竟這個國家與社會,將會走向何處?
2009年,研究者與熟人當中,仍然有人認為我選擇到臺灣而非美國做研究,是不智的選擇,並說:「你究竟想在即將被中國統一、走向終結的國家中學習些什麼?」對於將臺灣視為安心又安全的海外觀光地的日本人來說,日本政府在處理釣魚臺列島國有化問題,導致中日關係惡化,以及最近的反日示威遊行和暴徒橫行的中國報導裡,臺灣都像是與國際政治或外交對象完全無關。對於一出生就是日本社會上的少數與弱勢的我來說,在國際開發的現場或國際社會中,從組織體制外的弱勢者觀點進行思考,是不可欠缺的。此外,為了脫離戰後長期影響日本的美國式思考,從東亞的地理政治學觀點來看,前往未來必定會產生的中文圈學習,必然有其益處。話雖如此,我卻激不起興趣前往空氣汙染嚴重、限制民主主義研究的中國。臺灣的臺北已經有許多為了觀光或留學而居住的日本人,感覺無法定心進行研究。回想起來,到臺南還是正確的選擇。
於成功大學當訪問學者的期間,受林朝成教授、丁仁方教授、國立成功大學社會科學院以及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許多教職員的協助,使我得以進行臺灣市民社會的考察。透過觀察參與更加深我對於臺灣市民社會的發展,不只關於臺灣,還跟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的華人社會,以及中國的民主化產生關聯。而我的想法,在考察2014年3月至4月臺灣的太陽花學運中,學生們以和平方式進占立法院,以及其後政府和執政者的回應,還有7月與9月到10月,香港學生發起的民主化示威遊行之後,更成為不可動搖的確信。
納瑪達水庫問題之後筆者現在研究關心的議題,是與世界銀行的審查專家會議實際有效性的相關研究。為此,我曾前往印度、孟加拉、賴索托、巴西的亞馬遜、尼泊爾、柬埔寨、阿爾巴尼亞等地進行調查,並見聞巨型水壩、鋪路、造橋、拆除貧民窟、掩埋湖泊……等等,許多在開發中國家以蠻橫手段進行的開發案,以及受到開發影響的人民、減少的動植物種類、環境惡化等狀況—這當中有好幾個地方,都有中國援助的案例。
雷曼兄弟破產事件之後,經歷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以及加強反恐對策,美國的唯一超級大國地位,似乎快要被追過。追在其後的,正是有著巨大人口與市場的中國。世界銀行之於中國政府,不只是經濟實力相等的地位,也讓中國認為自己有責任援助,因此中國逐漸參與到國際社會當中,也就是中國期待成為名實俱符的「先進國」。從臺灣金門流亡到中國的經濟學家林毅夫,於2008年至2012年擔任世界銀行的上級副總裁
兼主任經濟學家,這是臺灣社會不陌生的事,而這與中國經濟的崛起不能說沒有關係。
在世界銀行的指導原則中,在環境、移住、原住民等方面都有相對應的規範。不過,由中國自行對開發中國家進行援助的行動中,幾乎不可能超越中國國內的準則。關於中國目前的進行方式,是中國會轉變為符合世界銀行的規範呢?還是世界各國要配合中國的新標準?必須抉擇的時間點就在不久的將來吧。目前中國正準備設立以新興國家為主的BRICs銀行,也稱為「亞洲投資銀行(AIIB)」。究其意圖,是為了挑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秩序和布雷頓森林體系。
以保守的日本政治與社會對中國的行為所能做出的回應來看,應該無法壓制中國的力量。不過,對於跨越國境的市民社會而言,以美國為中心過度發展的資本主義、以及中國的民主化都是持續不斷需要關注的問題。更何況是做為東亞島國的日本與臺灣,更必須自由地對這些議題進行議論。在這一層意義之下,臺灣是中文圈中,最能夠以言語和行動向中國發信的地方。臺灣和華人市民社會被賦予的責任十分重大。為此,若本書能發揮一些功效,筆者將十分高興
。
致群學出版社與編輯者的感謝
本書自翻譯企畫到出版,歷經四年的歲月。筆者在此向劉總編輯為首的群學出版社編輯群,特別是責任編輯沈志翰先生,以及翻譯者堯嘉寧小姐表達謝意。另外,也感謝許秀雲小姐的協助,許小姐為求能使本書盡早在臺面市,以使臺灣民眾理解本書的意義,協助與群學出版社保持聯繫。
段家誠
2014/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