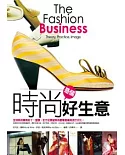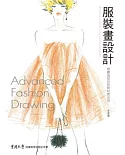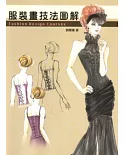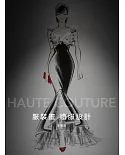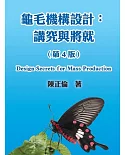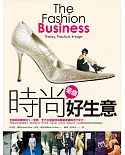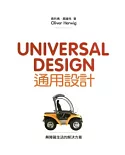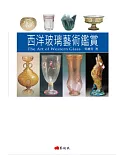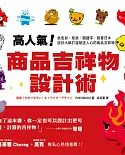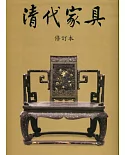台灣版作者序
字體溫
這本書的照片,是從二○○四年一直拍到二○○六年的照片。雖然是距今不久以前的事,但當時拍下的那些工作現場都已經不在了。當然,作為各自代表法國和日本的大印刷廠,這兩座大廠依然健在,唯獨活字版印刷部門消失。時代變化的速度,已快到連抓住瞬間剎那的攝影都要追趕不上了。尤其這本攝影集出版以來,已過一年,對此感觸更深。也就是說,拍攝本書照片的時期,雖然很短,然而,真正記錄下來的,難道不是漫長時間結束的?那?我感覺到,收錄在書裡的照片,似乎就在始於古騰堡的活字版印刷之漫長歷史結束,而印刷與書籍的新時代剛開始的時候記錄下來的。
被印刷出來的文字,是在人的手中耗費很長時間製作出來的。法國國家印刷廠,就是這樣的地方。從克勞德?加拉蒙設計鼎鼎大名的加拉蒙體開始,許多知名的字體都在這裡誕生。然而,不只是西歐字母而已,這座印刷廠製作從阿拉伯文、希伯來文到埃及象形文等全世界語文的活字,並以之印刷出許多重要典籍。
封面使用的照片就是來自那些典籍中的一本,即史上最初的漢法拉文辭典,雖然是拿破崙一世敕令編纂的辭典,但是用以印刷該辭典的中文字,則是在皇家印刷廠耗費大約一世紀的歲月雕刻的木活字。儘管說那是歐洲人首次嘗試將中文系統化的成果,但翻閱法國國家印刷廠僅存的一本《漢字西譯》時,我卻體會到與這段歷史有別的另一番不可思議的感受。
收在該書的中文字,有很多是現在已不使用,直到翻開那一刻才第一次目睹的東西。就所謂初相遇的這層意義下,對十八世紀的法國人而言,照理說應該也是同樣的感覺,但他們注視文字時,或許是帶著獨特的感覺雕刻出理想造型的字體吧。那些活字顯露出,每一個字都儀表堂堂,都是一筆一劃認真雕刻出來的字。或許因為我是熟悉篆刻的東方人,所以會有這種感覺。不過,就在讀著那些中文字的法文與拉丁文翻譯註解,想像文字橫度的迢迢遠程旅行時,我領略到,活字本身也擁有生命。
這種感覺與一般的意象也許相反。因為,比起親筆手寫的字,金屬活字給人的感覺通常只是機械般的冰冷罷了。但是,不管是哪一個活字,都和人一樣擁有獨特的履歷:字體原型被雕刻出,然後母型被翻製出來,然後將高熱中熔解的合金灌進模型,而製作出鉛字,這是製作的過程;更進一步地,檢字、排版、一再地試印調整,這是印刷的過程。在這些過程中,人們一直是左右相反地盯著文字、並這樣雕刻、檢選文字。一個文字裡,就隱藏著許多獨特感覺的手和眼睛。而且,有時甚至連時代、地點都相隔遙遠,而彼此陌生的人之間的身體與感覺,就濃縮、凝聚在一個文字裡。
因此,無疑地,不管是哪個活字裡,都有各自的體溫。那也是在有限的時空下,思慮如何有效率地製作、印刷漂亮文字的,既沉靜又熱情地向智慧挑戰的溫度。我在拍攝那些最後的現場時,同時確信,縱使活字被棄不用,活字永遠都懷著一顆溫暖的心等待著。
活字裡保存著特定時空下人們眼裡與手中的記憶。即使已到所有書籍都能從網路上閱讀的時代了,相信這份記憶不會因此就消失。不如說,與產生此記憶的時空分開存在的電子化書籍,正是因應如此的新時代而誕生的吧。
而這份記憶的一部分,又在擁有豐富漢字文化的台灣出版,對筆者來說,對這本書來說,都是無比的幸運。我由衷地感謝為嶄新的旅行開啟門扉的出版社與譯者。
二○○八年 於巴黎 港 千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