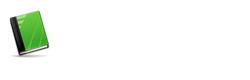胡適與蔣介石同道相謀反共,但比蔣介石更為徹底和極端。
繼《舍我其誰:胡適,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舍我其誰:胡適,第三部:為學論政,1927-1932》後,江勇振教授推出《舍我其誰:胡適,第四部:國師策士,1932-1962》。
1932至1962年這段期間,是胡適一生當中最被人誤解、不解與亂解的階段,胡適跟蔣介石同道相謀反共,但比蔣介石更為徹底和極端。
《國師策士》是四部曲的《舍我其誰:胡適》系列的完結篇。
這部完結篇所分析的,是胡適一生當中最被人誤解、不解與亂解的幾個階段:包括他1930年代的政治學術思想、擔任中國駐美大使時期的言論與作為,以及從國共內戰到蔣介石敗走台灣以後的所作所為。
胡適和蔣介石同道相謀反共。他們之間的不同,是蔣介石心知要反攻大陸就必須靠美國,但在嘴巴上就是不肯承認;胡適則明白宣示他「苦撐待變」的真諦,是在等待美國發動全球性的反共聖戰,以便一舉反攻大陸,甚至直搗國際共產的老巢莫斯科。胡適的反共,比蔣介石更為徹底和極端。
胡適不但是美國思想脈絡之下的冷戰鬥士,他更是美國冷戰鬥士裡的冷戰鬥士、美國冷戰鬥士的鷹派裡的鷹派。晚年的胡適不是「自由主義者」這個籠統的字眼所能形容的。他是美國脈絡之下的「新保守主義者」。這種保守主義不是西方傳統的保守主義,而是以確保美國霸權為宗旨的「新保守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