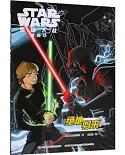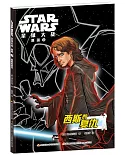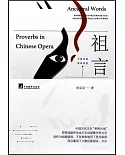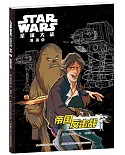這是一部以列傳的的形式書寫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史。
馮雪峰、聶紺弩、巴人、孟超、牛漢、樓適夷、嚴文井、韋君宜、綠原、舒蕪、林辰、秦兆陽、蔣路┅┅這些名字,不僅深深地嵌入了風雲變幻的中國現當代文化和文學的歷史,而且也與北京朝內大街166號——人民文學出版社息息相關。
剛直,狂狷,率真、超然、勇毅,豎韌,倔強,謙和,篤實┅┅他們中的每個人都足以構成一個社會單元,富於獨立的精神文化價值; 但當作者面對眾多的人生畫面,鉤玄提要,有機鋪陳,在展現歷史的同一性時,則更具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這是人格的力量,這是悲劇的力量,更是理性的力量。
序
當「知識分子」的名詞輸入中國之際,正值這塊古老的東方大陸艱難轉型。由傳統士人蛻變而成的現代知識分子,歷史負擔無疑是沉重的,然而,他們卻以曠古未有的英雄主義行動,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辛亥革命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實質性成就,無論以多少富含黃金的字眼去形容它,評價它,都不會過分。即便如此,支配了幾千年的封建專制主義勢力對知識分子的影響依然強勁。即以五四以後的頭十年為例,從無政府主義到「好政府主義」,從「到民間去」到「踱進研究室」,從「為人生的藝術」到「為藝術而藝術」,都是明顯的轉向和倒退。一代啟蒙工作陷於停頓。大的方面原因有兩個:一是知識者的先天性脆弱,一是社會運動漸成壓倒性優勢,總之,知識精英與社會大眾不是分頭並進,而是由後者瓦解和吞並前者,使之喪失曾經一度在斗爭中獲得的獨立身份。及至後來,整個知識群體幾乎淪為「社會公敵」而遭到唾棄,如「文化大革命」,其受迫害的程度是驚人的。
知識分子的命運史,其實是一部中國現代化史,是一段相當漫長的「苦難的歷程」。
書寫知識分子的歷史是意義重大的。然而,這種近於集體自傳式的書寫,惟有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才成為可能;在此之前,實在是只可為政治家或工農兵立傳的。遺憾的是,有了史傳之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大多未能如實反映知識分子的面貌。對於歷史,我們不是采取歷史主義的態度,相反以意為之,功利主義得很。在否定知識分子改造運動之余,走向另一個極端,極力掩蓋知識分子自身的人格和思想方面的缺陷,掩蓋知識與權力的關系,故意誇大個別政治文化派別或學術小圈子的成就,如二三十年代的「英美派」(「現代評論派」-「新月派」)、九十年代的「自由主義」和「新左派」,制造知識分子神話。如此種種,有一個帶根本性的原因,就是知識分子自我批判意識的缺失。
王培元先生長期以來一直關注知識分子問題。十多年前,他即已撰寫了一部延安「魯藝」文藝史;這本《在朝內166號與前輩魂靈相遇》的出版,可以看作是作者關注四十年代知識分子的事業與命運的一種延續。不同的是,前者側重事件,後者聚焦人物;但無論擇取何種結構方式,作者都不是從觀念出發,而是從事實材料出發,盡可能讓塵封的檔案及鮮活的記憶直接說話。
本書是王培元先生為所在的人民文學出版社老一代知識分子撰寫的列傳。這是一家身份特殊的出版社,素有「皇家出版社」之稱,從中央到地方的金字塔式的建構來看,它居於塔尖的位置,是出版界精英人物最集中的地方。他們的沉浮進退,在中國知識界中是具有代表性的。
列傳,是創自《史記》的一種傳統的歷史書寫形式。在史書中設置列傳,它的好處是將歷史文學化、人性化,通過人際關系的展開和人物形象的刻划,賦予歷史以政治、軍事以外的豐富生動的生活內容。王先生的書不是那種傳統意義上的嚴謹的史學著作,而是一部融合了史學與文學因素的邊緣性著作。全書由多篇獨立的小傳連綴而成,它的歷史性,主要表現在不同的個人命運背後的共同的時代框架上面。整個框架大象無形,然而堅硬實在,不可變易。書中的人物幾乎無一可以免除批斗、囚禁、勞役,深受精神和皮肉之苦,簡直帶有宿命的性質。其中,孟超和巴人的結局,可謂慘絕人寰。他們其中每個人都足以構成一個社會單元,富於獨立的文化價值;但當作者把這眾多的人生畫面有機地鋪陳開來,從而展現歷史的同一性時,顯然更具震撼的力量。這是悲劇的力量,也是理性的力量。
這樣,人類的價值與尊嚴便進入了全書的核心。正如我們在書中看到的,在政治壓力面前,中國的知識分子並不如西方知識分子那樣奮起反抗,而是忍耐、等待、掙扎,退回到自己的內心,惟以沉默的超重的工作體現自身的價值。作者沒有就「知識分子意識」,即在公共性和道義感方面向主人公們進一步提出質詢,也許他有感於苦難的過分深重,而視此為一種苛責,所以表現相當寬容。不同於那些知識分子神話制造者的是,作者不是先驗地去完成一個政治構圖,而是透過特定的生存空間接近他筆下的人物,在價值取向上,對某些傳統道德和人格規范表示認同。他固然贊美馮雪峰、牛漢的剛直不阿,欣賞聶紺弩的狂狷,樓適夷的率真,嚴文井的超然,感動於韋君宜的勇毅,蔣路的謙和,林辰的篤實,而對一度千夫所指的舒蕪,也在大關節處有所開解,不乏獎譽之辭。
大量的口述材料的使用,使全書具有為一般的考據史學著作或文學雜記所沒有的文獻價值。而這些材料,又是為作者所嚴加選擇的。其中,如毛澤東與馮雪峰的關系的變異,馮雪峰為《魯迅全集》作注,以及後來的焚稿;牛漢與艾青在批判會上的問答;秦兆陽夜訪劉白羽;嚴文井對趙樹理和周揚的評價;綠原學習外語的始因;樓適夷的懺悔;聶紺弩寄巴人詩及其不同版本等等,這些史料都是非常珍貴的。要在有限的篇幅中寫盡一個人的一生,這是困難的事。作者的寫作策略是:一來引入日常生活的材料,凸顯人物個性,二是發掘人物的文化價值的特異性;除此以外,都屬多余枝節而被刪夷。所以即使全書寫了十余位同樣職業的知識者,也不至流於面目模糊,彼此雷同。在書中,雖然作者使用了一定的文學手段,但是他並不特別看重為傳記作家所倚賴的情節,卻是較為注重細節性材料,由此顯出描寫的本領。書中的文學性,實際上更多地表現為富於文采的敘述語言。不同於歷史的分析性話語,作者是熱情的,激憤的,悲憫的,言語間有一種情感的浸潤;當人物的命運出現戲劇性轉折時,書中往往出現大段奔突而來的抒情性獨白,誠摯感人。
知識分子的歷史,需要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逼近真實,需要有不同形式、不同風格色彩的書寫。《在朝內166號與前輩魂靈相遇》僅系其中的一種。王先生囑我作序,使我得以重睹一群老知識分子的人生滄桑。我生也未晚,當「文革」時,受過批斗,坐過囚室,且累及家人,然而不要說為天下蒼生憂,其時竟連為自己抗爭的勇氣也沒有。這種懦怯一直延至今日,自覺是沒有為本書作序的資格的。以上文字,讀後感而已,倘若王先生以為可以印出來,那麽,就當是大時代里的一個小人物所作的一份精神見證吧。
知識分子的命運史,其實是一部中國現代化史,是一段相當漫長的「苦難的歷程」。
書寫知識分子的歷史是意義重大的。然而,這種近於集體自傳式的書寫,惟有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才成為可能;在此之前,實在是只可為政治家或工農兵立傳的。遺憾的是,有了史傳之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大多未能如實反映知識分子的面貌。對於歷史,我們不是采取歷史主義的態度,相反以意為之,功利主義得很。在否定知識分子改造運動之余,走向另一個極端,極力掩蓋知識分子自身的人格和思想方面的缺陷,掩蓋知識與權力的關系,故意誇大個別政治文化派別或學術小圈子的成就,如二三十年代的「英美派」(「現代評論派」-「新月派」)、九十年代的「自由主義」和「新左派」,制造知識分子神話。如此種種,有一個帶根本性的原因,就是知識分子自我批判意識的缺失。
王培元先生長期以來一直關注知識分子問題。十多年前,他即已撰寫了一部延安「魯藝」文藝史;這本《在朝內166號與前輩魂靈相遇》的出版,可以看作是作者關注四十年代知識分子的事業與命運的一種延續。不同的是,前者側重事件,後者聚焦人物;但無論擇取何種結構方式,作者都不是從觀念出發,而是從事實材料出發,盡可能讓塵封的檔案及鮮活的記憶直接說話。
本書是王培元先生為所在的人民文學出版社老一代知識分子撰寫的列傳。這是一家身份特殊的出版社,素有「皇家出版社」之稱,從中央到地方的金字塔式的建構來看,它居於塔尖的位置,是出版界精英人物最集中的地方。他們的沉浮進退,在中國知識界中是具有代表性的。
列傳,是創自《史記》的一種傳統的歷史書寫形式。在史書中設置列傳,它的好處是將歷史文學化、人性化,通過人際關系的展開和人物形象的刻划,賦予歷史以政治、軍事以外的豐富生動的生活內容。王先生的書不是那種傳統意義上的嚴謹的史學著作,而是一部融合了史學與文學因素的邊緣性著作。全書由多篇獨立的小傳連綴而成,它的歷史性,主要表現在不同的個人命運背後的共同的時代框架上面。整個框架大象無形,然而堅硬實在,不可變易。書中的人物幾乎無一可以免除批斗、囚禁、勞役,深受精神和皮肉之苦,簡直帶有宿命的性質。其中,孟超和巴人的結局,可謂慘絕人寰。他們其中每個人都足以構成一個社會單元,富於獨立的文化價值;但當作者把這眾多的人生畫面有機地鋪陳開來,從而展現歷史的同一性時,顯然更具震撼的力量。這是悲劇的力量,也是理性的力量。
這樣,人類的價值與尊嚴便進入了全書的核心。正如我們在書中看到的,在政治壓力面前,中國的知識分子並不如西方知識分子那樣奮起反抗,而是忍耐、等待、掙扎,退回到自己的內心,惟以沉默的超重的工作體現自身的價值。作者沒有就「知識分子意識」,即在公共性和道義感方面向主人公們進一步提出質詢,也許他有感於苦難的過分深重,而視此為一種苛責,所以表現相當寬容。不同於那些知識分子神話制造者的是,作者不是先驗地去完成一個政治構圖,而是透過特定的生存空間接近他筆下的人物,在價值取向上,對某些傳統道德和人格規范表示認同。他固然贊美馮雪峰、牛漢的剛直不阿,欣賞聶紺弩的狂狷,樓適夷的率真,嚴文井的超然,感動於韋君宜的勇毅,蔣路的謙和,林辰的篤實,而對一度千夫所指的舒蕪,也在大關節處有所開解,不乏獎譽之辭。
大量的口述材料的使用,使全書具有為一般的考據史學著作或文學雜記所沒有的文獻價值。而這些材料,又是為作者所嚴加選擇的。其中,如毛澤東與馮雪峰的關系的變異,馮雪峰為《魯迅全集》作注,以及後來的焚稿;牛漢與艾青在批判會上的問答;秦兆陽夜訪劉白羽;嚴文井對趙樹理和周揚的評價;綠原學習外語的始因;樓適夷的懺悔;聶紺弩寄巴人詩及其不同版本等等,這些史料都是非常珍貴的。要在有限的篇幅中寫盡一個人的一生,這是困難的事。作者的寫作策略是:一來引入日常生活的材料,凸顯人物個性,二是發掘人物的文化價值的特異性;除此以外,都屬多余枝節而被刪夷。所以即使全書寫了十余位同樣職業的知識者,也不至流於面目模糊,彼此雷同。在書中,雖然作者使用了一定的文學手段,但是他並不特別看重為傳記作家所倚賴的情節,卻是較為注重細節性材料,由此顯出描寫的本領。書中的文學性,實際上更多地表現為富於文采的敘述語言。不同於歷史的分析性話語,作者是熱情的,激憤的,悲憫的,言語間有一種情感的浸潤;當人物的命運出現戲劇性轉折時,書中往往出現大段奔突而來的抒情性獨白,誠摯感人。
知識分子的歷史,需要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逼近真實,需要有不同形式、不同風格色彩的書寫。《在朝內166號與前輩魂靈相遇》僅系其中的一種。王先生囑我作序,使我得以重睹一群老知識分子的人生滄桑。我生也未晚,當「文革」時,受過批斗,坐過囚室,且累及家人,然而不要說為天下蒼生憂,其時竟連為自己抗爭的勇氣也沒有。這種懦怯一直延至今日,自覺是沒有為本書作序的資格的。以上文字,讀後感而已,倘若王先生以為可以印出來,那麽,就當是大時代里的一個小人物所作的一份精神見證吧。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131
-
二手書$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