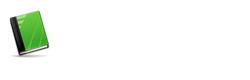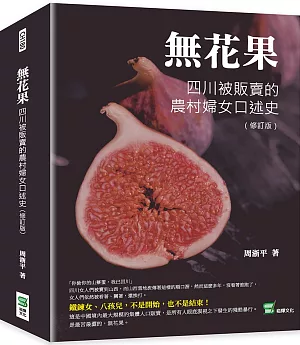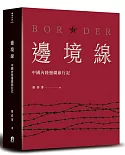序
無可選擇的命運(導言)
正在發生的,也正在成為歷史。中國新政策以一九七九年為起點,宣布摘掉地主、富農、資本家、右派等各類反動階級、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為特徵,放棄了堅持幾十年的階級鬥爭政治方針,一九八〇年以承認私人商販合法性為特徵,準備放棄仿效蘇聯的中央計劃經濟的經濟政策,開始進入了一個以經濟為中心的階段。平魯縣(一九九〇年改為區)一九七九年出現了第一個以分「口糧田」為由實行「分田單幹」的生產隊,郭家窯公社薛家窯大隊。一九八〇年冬,大部分生產隊效仿,將集體土地分等劃級,抽籤「分田到戶」,一九八一年的春播是在家家戶戶的承包地上開始的。在一九八三年政府宣布取消人民公社組織前,公社和生產隊已是名存實亡。此時束縛在農民身上的集體組織紀律同時瓦解。
口述人敘述的這段歷史就是在農民獲得自由之身後同步發生的,一直持續到二十一世紀初。訪問者從受訪者口中了解到,販賣女人買賣雙方的地域涉及中國雲南、貴州、四川、湖南、湖北、安徽、甘肅、陜西、內蒙、山西、山東、河北、河南數省。買賣女人的數量雖無法統計,僅以平魯為例,全縣四百五十二個(一九八四年)自然村,買女人的農民,一村少則一、二人,多則二、三十人。由此窺見一斑。一個女人的價格,一至五千元不等。二〇〇八年九月,訪問者在計家窯村親見買賣的現場,二個四川昌都地區的男青年領著三個女人在出賣,在四小的家裡,三個女人坐在炕上,下面站滿了一窯人,觀看、評論,年齡最小的開價兩萬元,年齡最大的,看上去約摸三十多歲,開價三千元。販賣者是由四小的媳婦引來的,她也是四小花五千元買的,姓名、年齡均不知。四小媳婦操的語音無人能聽懂,我懷疑是某種少數民族語言,當我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再次來訪,準備向東水窪村一個四小媳婦的同鄉求證時,她會說漢語,卻得知她們雙雙均已留下生下的孩子離去,當地人的說法是跑了。從訪問的各村情況判斷,跑了的女人約占三分之一到半數間,跑的原因各有不同。按四小的說法,給他生了個兒子跑了,錢花得值。
無論賣家、買家,還有當作商品的女人,在二十多年的時間裡如此多人捲入其中,只為了錢,或出路,釋放的人性撕去所有法律、道德、親情的遮羞,赤裸裸地行走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人們不禁要問我們不是自由了嗎?再沒有農業社集體化的紀律約束了,可以透過自己的努力獲得小康了嗎?怎麼會成了這樣,我們成了一群毫無良知的行屍走肉。被捆綁和壓抑了三十多年的人性,原本不該是這個樣子,是什麼力量讓在禁錮中的人性扭曲變形了,三十年後釋放出來不覺意間害人害己。過去的三十年中每個人被削足適履的要求做一個無私的人、高尚的人,做一個共產主義的新人,三十年後削去的部分不但沒有被埋葬,適得其反,膨脹變形,而被詞語汙染的舊道德卻被踩在腳下,不見了蹤影。但,我們完全沒有必要對眼前景象故作驚訝,而有意無意忽略了別樣的真相。
販賣女人的話題,在我近十年做「平朔農民口述史」的時間內常有談及,無論平魯還是朔縣,受訪者多會談到誰或本人娶的是四川女人或「侉子(外鄉人,貶義詞)」。所謂「娶」,就是買的另一種表述,因為娶女人,一要舉辦事(婚)宴,二要辦理婚姻登記手續,而買一個外省女人做媳婦,這兩樣都被有意取消了。對外而言,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在村子內,村民採取了配合接受的態度,沒人提出異議。當地政府改採的態度很曖昧,除去一九九五年山西省省委書記提出北部縣市集中打擊拐賣婦女的一次行動,其餘時間基本放任。政府幹部們,包括警察都繞著走,偶有明晰的線索,被賣女人的家人投訴追尋,進村調查難度大,村民相互遮掩。一九九五年平魯在打擊拐賣的行動中,被「解救」的拐賣女人二百餘人,公費返鄉,卻有部分女人因對已生子女的牽掛,回鄉後又自費返回。因此有人說,政府的行動拆散了很多家庭。
販賣女人的情況恰恰出現在有組織、有紀律、有計劃的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管理方式終結的背景下,是各種因素綜合發生影響的結果。習俗、道德、人情、法律、政策等內容的考慮交織在一起,出現使用買女人的方式產生的不合法規的家庭普遍存在的事實,隱性的反映出這類家庭成員對女性、家庭訴求的某種急迫、不安、恐懼、隱藏等複雜的心理。就在我此次專訪的第一天,在東水窪村訪問了三名川籍婦女回到住所的當晚,帶我進村的人就接到東水窪年輕村長的電話,據他說被訪婦女的丈夫找他談,說我這是要幹什麼,這會破壞他們的家庭夫妻關係。我並不相信他的話,因為在我作訪談時她們的丈夫均在場,在整個受訪過程中沒有表示任何異議。這個村長為什麼要這樣做,他阻止我訪談的動機是什麼?東水窪村最早發生買女人的事應在一九八〇年代初,他不過是個十來歲的孩子,對三十多年前發生的事為何如此緊張?在我第二次進村訪問時才明白了個中緣由,這次接受訪問的孫天謀、陳匯榮夫婦正是村長的三爹(三叔)、三媽(三嬸),他的四爹正是這個村第一個娶四川女人的人(此時已搬離村子)。他要維護的正是家族親友的家庭,並非什麼正義。這不是我遇到的唯一有此顧慮的人。
經過一次訪談就會產生動搖這類家庭的夫妻關係,有如此虛弱的心理陰影,可見一些人對買四川女人成家歷史的不踏實感還罩在心頭。這不僅存在於買女人這一方的人群中,還存在於一些被賣一方的女人中。經過第三者聯絡,一些四川籍婦女乾脆拒絕訪問,一句「沒有什麼可說的」,緊緊鎖住心理的大門。當訪問者已來到受訪者面前,在說明來意後,一位雙碾村的川籍婦女三句話結束了談話,「現在生活很好,在這兒很習慣,我正忙著呢」。用各種話語拒絕深談的女人不止一、二位,有的還顯得態度粗暴。她們以這樣的方式我以為是在保護自己,告知娶她們的當地人不會說出她是被賣來的。他們要隱藏的除去買賣雙方都想隱藏的部分,可能還有會引起家鄉親友不安的部分。
傷疤只有揭開了,才能治癒,捂著就會繼續發生陣陣隱痛。受訪者李小霞明確告訴訪問者,這段歷史到該說出來的時候,她的子女、家人都該知道,這段歷史已經過去,說出來是為了過好當下的日子。隱去姓名的一位受訪者,在講出她當年以被賣的方式賺錢,最終不忍騙對方,選擇留了下來,自己把自己賣了的經過。她願講出,希望訪問者寫出來,告訴世人,但她的子女不知道她的歷史,不同意留下她的影像,以免影響子女的生活。她的心思讓人動容。事後她還給介紹訪談的同鄉說,她的談話讓她出醜了。面對過去,她們不是後悔、怨恨,訴說時會心痛,流淚,但畢竟過去了,日子還要過下去,更要操心的事情是兒孫的生活,家庭的收入和未來。
在接受訪談的四十九位川籍、五位甘籍、三位滇籍、一位陜籍、一位晉籍婦女的家庭中有一個共同點,她們現在的生活基本屬於常識認識的正常狀態,雖不能按當地人的說法都處於「好活」(幸福)的時候,但與多數農村家庭比較沒有什麼大的差異。當訪問者在傾聽她們敘述的經歷時,自然地想到托爾斯泰曾描寫一位婦女生活時寫到的一句話:幸福的家庭都一樣,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她們的境遇是現在的「幸福」家庭也有各個不幸的經歷。初到時不能自由行走防逃離的看管,被當地人歧視不稱姓名為「四川侉子」的稱號,遭男人打罵更是家常便飯,成為沒有婚姻登記、沒有戶口的「黑人」等等。談到這些經歷,她們往往忽略一些細節,可能是忌諱家庭其他成員的感受,卻談出比她們更可憐、更悲慘命運的「她人」。如白辛莊村的一位川籍婦女,先後被賣過三次,頭一次賣到白辛莊村,二次賣到九坪梁村,三次又賣回白辛莊村,一個原因是當地人認為她是「愣子」(可能有精神疾病)。在最後這家,她被男人用鐵鏈子拴在文革時挖的防空洞裡,一年後她生下一個孩子,把她放出來,繼續拴在窯家裡,又生下一個孩子。這位不幸的女人,連「性奴」都算不上,只是一個性工具。我在二〇一五年九月還訪問過他的男人和婆婆,他們隻字未提。就在同一時間,九坪梁村也有這樣一位被「撿」回來的,連籍貫都搞不清楚的女人,給賈四當老婆。她們還談到大泉溝村、小川村的兩位川籍女人,被男人用羊鞭抽打,逼她們幹農活,小川村的那個女人被男人用鞭桿戳瞎了一隻眼還不放過,整日挨打。在她們的男人心裡,她們只是花錢買來的一個對象,不是人,不是和他們一樣的男人、女人。
被經濟學者稱作「市場經濟」開始運行的年代,出現買賣女人的現象不是一朝一夕偶然發生的個別刑事案件。蔓延數省、涉事數萬人口的販賣女人,首先與傳統積習發酵相關。傳統習俗女子出嫁要向男方家庭索要彩禮,民國時期的彩禮,多數為糧食、牲畜、衣妝等,農業合作化時期糧食統一平均分配,社員私養牲畜的種類、數量也被限制,彩禮多為現金,外加一、兩身衣妝,時尚的彩禮有縫紉機、自行車等控制商品,總的在計劃經濟配給商品供應的年代,索要彩禮的習俗,雖經在政府經常批判買賣婚姻的輿情下,也無法禁止。無論在那種環境中,在普遍貧困的背景下,對要娶女人成家的男方家庭都是不小的一筆支出,物質準備成為組成家庭的先決條件。在普遍貧困的年代,光棍必然就多,這種看上去女人優先的態勢,卻隱含著男女不平等的習俗觀念,只要你付得起彩禮,就等於你買得起女人,就可以享用你的夫權。出賣女子的家庭也是為了買回女子給在家的男孩。女子就成為婚姻中最重要的物質交換籌碼。一位老年婦女回憶年輕出嫁時的情景,曾講到她的父親和未來的公公當著她的面,兩人坐在炕頭上,雙方伸手放在衣襟下捏咕(暗暗比劃)討論身價,她說就像買賣牲口一樣。在買賣牲畜的集市上,雙方也是用這樣的方式討價還價,不能公開講價是不想讓第三方知道,以免影響可能存在的下一家買賣。就在一九八〇年代至一九九〇年代買賣女人最猖獗的時候,口述人曾經歷在四川一些縣鎮的茶館裡到處是買賣女人的掮客活動的場景。
由於歷史原因,在山西北部、內蒙南部、山東、河南、河北產生的大量光棍需要女人,在四川、雲南、貴州、湖南、湖北等省有大量想急於擺脫貧困生活的女子。人販子從中嗅到了商機,伸出了手。買賣女人成為一樁半公開的生意。介入到這樁生意中的人,包括圍獵可能被出賣女人的血親成員,父親賣女兒,兄弟賣妹妹、姐姐賣妹妹、姨姨賣侄女,這些人為了錢可以將親情拋在一邊。在一九九五年打擊拐賣婦女行動中,平魯判死刑的二十二名人販子中有二名女性,她們自身就是被賣到山西的女人,她們對深陷困境的感知是麻木不仁,轉身又對同性的同胞下手。據一位當時領導打拐行動的地方公安部門負責人講,判死刑的標準是販賣六名以上的人員。這些人中既有四川販賣女人到平魯的人,也有當地再從他們手中將販來的女人轉賣到各村中的人。成為一條生意鏈。
一些人誤解,以為賣出地的女人因為窮,是尋找出路的被迫之舉。這位公安人員講,買的地方同樣是窮,越是窮的地方,買四川女人的就越多,整個山西北部雁北地區,忻州地區二十多個縣都有涉及。逃離苦海的渴望,因又入苦海沒有絲毫改變。口述人歸納買四川女人的男人有三個類型,一是窮娶不起當地女人,二是有殘疾娶不上當地女人,三是歲數大娶不上當地女人。以當時糧價計算,主產的糧食有莜麥(裸燕麥)和豌豆,平均一斤售價二、三角,花三千元買一個女人,需要一萬五千斤糧食,平魯縣包產地人均六.二畝(一九八五年),畝產平均百斤,三千元需要二十三年的產量,一九八四年糧價放開後,以糧價翻一倍計,仍需十二年的產量。集全家之力,向親友借貸,才能買得起一個女人。據口述人講,至今還有因成家未還清借貸的家庭。平魯縣是有名的貧困縣,相鄰的朔縣同樣娶四川女人的農民也不在少數,只不過選擇性大些,除了四川來的,還有湖南、湖北、陜西的。集體化結束不久,普遍貧困的狀況還沒有大的改善,販賣女人的地域自然就廣。三十年後,這種差異才顯現出來。如有一種說法,朔縣外地女人跑的少些,是因為生活狀況比平魯強些。
許多受訪者在回答訪問者被賣後有沒有逃走的想法,或者是已經回到了家鄉怎麼又回來了的提問時,她們幾乎一致的回答是捨不得孩子,自己已經經了苦難,不想孩子遭同樣的罪,不能讓被迫母子分離的痛苦在孩子身上再經一遍。出於本能的母愛,使她們能忍受命運不公的結果,繼續接受未知生活的磨練。連娶她們的男人們也深知成了母親的四川女人們,為了孩子,她們就可能待下去,有了孩子的四川女人,就不再嚴管看守了。
在我接觸的受訪者中,賣來時最小的只有十二歲,大的不過二十歲,十五、六歲的居多。她們從溫暖氣候的四川,一下跌入寒冷的黃土高原地帶,舉目無親,被關在閉塞的山區窯洞裡,連方向都辨別不清,加上身無分文,逃跑是很難的。計家窯村的四個四川女人結伴,只能沿大路徒步出走,走了七、八十里路,還是給追回來了。有的被抓回來,還要遭到打罵,說再跑就打斷她的腿,嚇得不敢再有逃跑的念頭。一位受訪者描述她的困苦,說一晚她流的淚,滲透了蕎麥皮的枕頭,溼在了炕席上,回憶三十年前的情景,仍不輕鬆,依然是淚流當面。如此冷酷的現實,出生的孩子成了她們最柔弱的地方,同時也是她們最堅韌的地方。孩子是她們的希望,也是她們願意付出一切的寄託,包括自己青春的年月,再也回不來的年華。
在販賣女人的歷史中,她們由女孩變成了母親。她們經受了常人無法體驗的屈辱和苦難,她們挺過這樣的人生,支撐命運的動力就是母愛的付出,至今如是。當初誘騙她們來山西的人販子說,山西一年只種一季莊禾,苦輕(勞動強度),不像四川地方一年四季勞作,人生經驗尚淺的她們不知,苦重是不分地域的,生存的代價哪裡都一樣。分田單幹後,與農業社時期不同,女人幹的活是和男人一樣的,她們也學會了耕田、抓糞這類過去只有男人才幹的活。我在訪問東水窪村、東港村、劉井溝村、白辛莊村時,受訪者中都還在有放羊的活在幹,這種春、夏、秋、冬整日在山野裡受罪的營生,女人們也同樣承擔。我去劉井溝村的那天,零下十九度,山上的風大,特別的冷,李鮮榮還又買了一群羊,原本的羊群擴大到四百隻,都是為了孩子支付上大學的學費、生活費。政府從二〇〇二年開始推行的退耕還林政策,使得很多村子的地不讓耕種,農民只得另覓出路。四川來的女人們成為縣城及周邊工程打工隊伍中的不可或缺的群體,她們當小工,綁鋼筋、搬磚、運料。她們種樹,早上五點就出發,自帶乾糧、水,不見日頭才回,一天要幹十五、六個小時。我後十天的訪問,正是天太冷、地凍了,不能種樹了,才使我有機會訪問到這些口述人。
平魯人口中,被賣到當地做媳婦的女人們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她們從南方來到北方,在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裡,生兒育女,持家生活。三十年過去,她們也講著道地的平魯話,在人群中當地人也很難認出誰是四川女人。當我問她們那裡才是你的家鄉時,很多人沒有回答,是因為她們不知道怎樣回答,或者如她們所說,在那裡都是生活,或者是對家鄉的記憶還不到喚起的時候,她們的年齡多數不到五十歲,還沒有卸去家庭生活的重擔,沒有思念家鄉的閒暇,或者是家鄉留給她們的記憶不願訴說。我原以為她們對家鄉會有強烈的思念之情告訴我,在訪談中的內容卻告訴我們另外一種情景。由於貧困女孩子讀書的機會比男孩子更少,在她們的記憶裡就是割餵豬用的雜草、拾柴這些幹不完的活路。與平魯女孩不同的記憶就是「包產到戶」後,她們第一個念頭就是離開家鄉出門打工,這在平魯同齡女孩中幾乎沒有,這也給人販子騙她們出去打工販賣女人製造了機會,事實是很多陷入被販賣困境的女孩事件都發生在成都火車站附近有名的荷花池人市(勞動力市場)。所謂家鄉的回憶除去家庭歧視就是離家出走被賣,這就是她們對這個話題不感興趣的原因,美好的童年對她們來說是不存在的。
從女孩到女人,從女人到母親,有辛酸、有苦熬,有的苦盡甘來,有的還在受罪。對這樣的人生命運,對那些拒絕接受訪談說出來的人,可能心中仍懷有不平的念頭,但多數接受訪談的人已經覺得那段歷史是過去式,沒有什麼需要隱瞞的。隱瞞自己的悲痛,等於給製造悲痛的人留下繼續造孽的理由。個子矮小的鄭貴,在結束訪談後還問我怎樣才能抓住當年販賣她的人。她至今也不原諒那個人販子。那段歷史遺留下來的殘缺,至今仍在她們身上無法彌合。其中一些人,如郭應仙、夏秀紅、邱冬蓮、賈英、雷金蘭等人至今沒有戶口,成了沒有身分的「黑人」,這樣的人不在少數。在她們有機會可以回鄉與家人團聚的時候,卻因沒有身分證買到車票,被困守在當地。還有,如羅淑蓮的妹妹被人販子賣到何處,至今下落不明,渺無音訊。還有,如譚華珍從第一天賣到白辛莊村起,就遭到沒完沒了的罰款,非法同居罰款、非婚生子罰款、超生子女罰款等等。她們是所謂弱勢群體中的弱勢,她們受到的不公、不平等對待來自各方面,他們是人販子罪惡結下的苦果,她們沒有承包地,沒有醫療保險,沒有選舉權,更談不上有最低生活保障的可能。她們的生活開始好轉,是靠女性特有的堅韌性格取得的。
這段大肆販賣女人的歷史,就發生在農民從處於長期饑寒狀態下突然開始爭取獲得溫飽的關口,在集體化組織下壓制個人利益鑄成的扭曲人性,與「包產到戶」釋放出的人性成為人慾橫流的衝動相交織的背景中,實現溫飽目標成為農民的全部生活內容,赤裸裸地追求物質帶來的滿足,不顧忌任何道德和法規的信條。從一個國家至上、集體至上的極端秩序徒然轉入一個個人利益至上的極端秩序,一切該發生和不該發生的都發生了,買賣女人以一切可以交易的商品衡量,良心的譴責和法規的禁令就都被封鎖了。一個制度不能提供成員生存的基本保障不是一個好制度,一個制度為了滿足不斷增長的私慾不能提供道德與法律的秩序同樣不是一個好制度。對於從集體至上的歷史轉換為個人至上的歷史,李小霞說對於什麼是幸福,過去的窮日子與今天的好日子沒有可比性,今天的富裕與昨天的貧窮沒有因果關係,她今天住在一所溫暖的二層小樓裡,與她被賣的歷史無關,那是不該發生的事情。在這個一切向錢看的時代,在你獲得金錢的滿足時,所付出的精神代價是金錢買不回來的。造成惡德的事實,人們常說一句話,是過去窮怕了。於是,富人成了美德的代名詞,媒體的宣傳是「誰富誰光榮,誰窮誰狗熊」。那個村長的恐懼,就是怕失去錢買回來的女人們。可誰又為此失去道德秩序感到過恐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