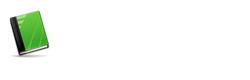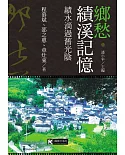雞窗夜靜思故友
「雞窗集」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一九八四年九歌出版社台北初版,我那時已六十三歲。在此前後所出的五種集子,皆以談論文學為主而少談到自己。香港七月剛出版的「談文藝,憶師友──夏志清自選集」倒是本道地的散文集,入選的二十篇中只有「上海,一九三二年春」、「紅樓生活志」、「外行談平劇」這三篇錄自「雞窗集」。「自選集」的台版即將由印刻文學生活雜誌社出版,本書的愛讀者不妨也買一冊看看。
林以亮(宋淇)為我寫的長序「稟賦、毅力、學問」也算是本書一個特色,因為我的其他文集只備自序,而從不請比我年長的師友寫篇序的。宋淇早在抗戰期間即是濟安哥的光華同學,且常來我家同我談話的。早於一九七六年我即為「林以亮詩話」寫了篇序,但宋淇兄一九九六年去世後,我因患有心臟病而並未在台港報刊上為他寫篇悼文。宋淇同我的另一至交高克毅兄都是香港中大「譯叢」(Renditions)的創業編輯(Founding
Editors)。「譯叢」一九七三年創刊。繼任他們的主編孔慧怡(Eva Hung)博士要於新世紀初出本慶賀該刊三十周年的紀念冊「譯叢點滴」(The Renditions Experience, 1973-2003),我也在被邀寫稿之列,寫了篇追念宋淇的短文("Remembering Stephen
Soong"),主要感謝他於一九四三年秋召集了一個文友聚會,給我機會同錢鍾書夫婦相見談話;再於五十年代初從香港寫封推崇張愛玲的信並把「傳奇」、「流言」此二書的盜印本也航郵寄我。我那時正在寫「中國現代小說史」,假如未能及時看到此二書,很可能我不會闢一專章去大寫張愛玲的。
除了宋淇那篇序文外,「雞窗集」還把琦君寫我的那篇「海外學人生活的另一面──讀夏志清『歲除的哀傷』有感」當篇「附錄」刊出。小女自珍一九七二年初出生之後,原先還看不出多少不正常,年齡愈增而其低智能和自閉症之病象愈顯,我和王洞為她日夜勞累而並不見她有何進步。「歲除的哀傷」既已提到了那晚父女摔交的實情,我想把琦君的讀後感當「附錄」刊出,也可讓讀者們知道我那幾年的生活實況,不必自己再操心去寫下那些痛苦的經驗了。
我於一九六二年來哥大任教之後,因為濟安哥的關係,最先認識的台灣朋友不外是他的台大外文系同事和學生。但時間久了,來自台灣而與先兄關係不深的訪美學者、作家我也認識了好多位。林海音就是其中的一位,她於一九六五年秋來美一遊,同我談及她要設立一個出版社,且創辦一份名叫「純文學」的月刊。我表示願意支持她,日後果然我的首三本文集都是交純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好多篇學術論文請人中譯後,也是先在「純文學」上發表的。
到了一九六六年初,我的第二部著作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中國古典小說)差不多已寫就,我在哥大已將教滿了四年,真想偕同妻卡洛、女兒建一到台北去住上半年,我一人初去台北當一名小公務員已是一九四五─四六年的事了。正好中日語文系已請到了一筆Fulbright-Hays獎金,可供我全家遊覽東京、京都兩週,居住台北半年。
吳魯芹兄嫂早已遷居華府了,約定在松山機場迎接我們的乃是先兄另一好友侯健教授。他先帶我們到台北鬧區一家館子點了一道一鴨三吃,大家吃得很滿意,再乘車送我們到圓山飯店住了兩晚。我那時只是個副教授,住了兩晚即遷居自由之家,再託林海音找一個公寓房子賃居。我在圓山飯店頭一個晚上即買了一罐五十枝裝茄力克牌(David
Garrick是英國十八世紀最著名的演員)香煙抽一兩枝自娛。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英國老牌茄力克即是上海最名貴的香煙而我從未抽過。同一晚上我也買了一冊台北翻印的邱吉爾名著「英語民族通史」(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至今還放在我客廳書架上。因為扉頁上寫下了初抵圓山的日期,才確定它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卅日無誤。
林海音很快即在金華街給我們找到了一套相當寬敞的公寓房間,可能是琦君給她的情報,因為她同夫婿李唐基兄即住在同街一幢二層樓的寓所。不少作家因慕我名或有求於我才同我相識的。但我同琦君一開頭就有了個鄰居的關係,再加上琦君雖是溫州人,她在求學期間杭州、上海、蘇州都住過,她可以用吳語、英語同我談話,友誼的增進也就更為方便。因之琦君每贈我一冊新出的文集,即使我已重返紐約,我自然而然想看,而且幾天內即把它畢讀了。沒有人請我寫篇文章評她,我當然也無意為她寫篇專論,但我於一九七四年在「書評書目﹂第十七期上看到彭歌「琦君的『煙愁』」這篇書評後,也就忍不住要把自己想說的話寫成一封信,發表於「書評書目」的下一期。我在信?把琦君同古今四位名家(三位是女性)相提並論:
琦君的散文和李後主、李清照的詞屬於同一傳統,但它給我的印象,實在更真切動人。詞的篇幅太小,意象也較籠統,不能像一篇散文這樣可以暢表真情。第一流的散文家,一定要有超人的記憶力,把過去的真情實景記得清楚。當年蕭紅如此(她的回憶錄「呼蘭河傳」是現代中國文學經典之作,實在應該重印),現在張愛玲如此,琦君也如此。
「琦君的散文(「書簡」節錄)」早已收入了我的第三本文集「人的文學」,此書即將由麥田出版公司重印。在我退休之後而尚未患有心臟病之前,我受梅新之託,寫了一篇長文「母女連心忍痛楚──琦君回憶錄評賞」在「中央日報」副刊上連載了三天(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八日─十日)。同時「中副」也舉辦了一個老作家討論會,我那篇論文也是討論的對象,唐基、琦君特從紐約趕來,參與此盛事。到了今天,那天下午在會場上發言的卜寧、王藍皆已物故,連遠比我年輕的梅新弟也早已病逝,琦君姊自己也於今年六月七日長離人世了。「中副」銷路不暢,當年看過「母女連心忍痛楚」此文的人數不一定太多。我當儘快出本新集,讓更多讀者能看到我對琦君散文的「評賞」。
寫本文時,我們兄弟的好友吳魯芹當然也在我思念之列,但我早已為他寫過三篇長文:「『師友?文章』序」見「人的文學」,「雜七搭八的聯想──『英美十六家』序」和「最後一聚──追念吳魯芹雜記」則同見本書,實在沒有必要在新序?為他多說些什麼了。他的毛筆字寫得瀟灑自如,行家見了都應該很喜愛。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日魯芹(名鴻藻)從台北美國新聞處寄給住在溫州街五十八巷台大宿舍濟安哥的那封「邀戰書」*,我在他遺物中發現之後,保存至今。「雞窗集」重版,我特囑蔡文甫兄把此函影印出來,讓讀者們看到魯芹兄另一方面的才華。
紐約,二○○六年九月六日
原書序
雞窗夜靜開書卷
一九八二年初,香港劉以鬯先生為我出了一本集子,題名「印象的組合」(香港文學研究社)。那是本選集,所選八篇錄自我已出版的四種集子(「愛情、社會、小說」、「文學的前途」、「人的文學」、「新文學的傳統」),算不上是本新著。事實上,「新文學的傳統」出版至今差不多已五整年了,五年來我中英文文章照舊寫,卻不知為何一直抽不出空來,把已發表的中文文章,結集出書。兩年多來,九歌出版社社長蔡文甫兄每有信來,總要提醒我一聲,新文集的稿子整理好了沒有,請速寄來。今年一放暑假,我就把這本集子整理出來,實在覺得再不繳卷,要得罪朋友了。之後我又重校「中國古典小說」(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的中譯本,想於九、十月間把改正本交遠景出版社出版。六七年前已看到了書的清樣,今年再不把譯文細加修改,我更對不住該書的主要譯者何欣教授了。五年來發表的文學評論,也早夠出本集子,但校閱「中國古典小說」譯本工程浩大,看樣子今年無時間整理另一本集子了。
「雞窗集」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性質同已出版的四種文學論評集不太一樣。本書第三輯「憶友談書」凡四篇,此類散文誠然在以前的文集?也出現過。但第一輯「自傳的片段」四篇,第二輯「迷上電影也看戲」五篇,也都是一無論文味道的散文(informal
essays),因之整本書的內容無非是我的回憶、感想,和偏見。第一、二輯的文字,我原想多寫幾篇,出兩本書的,一本專談我自己,一本講電影。但今年雖已六十三歲,我七十歲才退休,在哥大教書期間,總想多做些中國文學方面的研究,也就不逼自己去寫本自傳和專談電影的書了。此兩類文章,反正隨時有空都可以寫。
好多讀者知道我原先專攻英美文學,後來才改行研究中國文學的。其實,早在中學時代,我最感興趣的一門學問是美國電影。二十二年前定居曼哈頓以後,多有機會看舊片,重新提高了我研究美國電影的興趣,連帶也注意到英、德、法的早期名片,雖然談不上研究。我生平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即講電影,題名「好萊塢大導演陣容」,曾在上海「新聞報」副刊連載兩三天。那時我才高中畢業(一九三八年),或者剛念完大一,確切年份實在記不起來了。那時研究電影的英文書籍根本沒有幾種,僅有的那幾種我也看不到。一般影迷雜誌(fan
magazines)登載明星照片,講些明星私生活,對電影藝術並無真興趣。我不僅對明星有興趣,對導演、製片人、攝影師、編劇人都有興趣,至少把這些人的名字記得很熟。我那篇文章評介二十七、八位導演,沒有參考書可看,全憑自己看電影、看說明書、看影迷雜誌累積的經驗,實在很不容易。回想起來,三十年代的名導演,應該提名而我未加注意的,簡直沒有。華爾虛(Raoul
Walsh)晚年頗享盛名,但此人四十年代開始才給華納公司拍了好幾部名片,我在三十年代後期對他未加注意,沒有錯。
年紀輕記性好,我寫那篇文章時,對好萊塢八大影片公司的情形可說瞭如指掌。後來改行教中國文學,真不免有些羨慕古文根柢比我深厚的那幾位留美學人。假如我也同他們一樣,生在書香之家,從小有嚴師逼著讀古書,練寫詩詞駢賦各類文體,該多麼好!但現在想想:當年國學基礎打結實了,可能對西洋文學興趣就淡了,對外國電影更是不屑一顧了──我就不是我,變成另外一個人了。我至今覺得自己很幸運:先治西洋文學,再攻中國文學,一點也沒有走冤枉路。時至今日,不會填詞寫舊詩,沒有什麼難為情,但一個研究我國傳統任何一方面的學人,假如他對西洋文化並無較深入的了解,就吃了很大的虧。
第二輯討論電影的幾篇文章,寫於七八年前。七八年來,老電影看得更多,新片子也每年看幾部,假如我寫的是學術論文,有些意見就非修正不可了。譬如說,有一篇文章?我對馮史登堡批評了幾句。他有兩三部無聲名片我至今尚未看到,但近年來我看了他導演的「美利堅慘史」(An American Tragedy,德萊塞小說改編)、「罪與罰」(彼得勞雷主演)和The Scarlet
Empress(瑪琳黛德麗演俄國凱塞琳女皇,一九三四),對他好感倍增。「緋紅色的女皇」尤其是部罕見的歷史佳片。馮史登堡僅憑此片,應該名垂不朽,何況他還拍了三四部值得回味的精品。
一九七七年底霍華?霍克斯逝世,我寫了篇文章紀念他。三四年前,希區考克、威廉?偉勒相繼去世,我卻沒有寫文章紀念他們。沒有別的理由,就是沒有時間去寫,也沒有人逼我寫。希區考克的電影我看過二十七部(包括一部無聲片),偉勒的十八部,其中挑幾部特別心愛的談談,就是很像樣的兩篇文章。此類文章現在沒有空寫,希望有朝一日能寫出來。其實本書第一、二輯?的文章,對我來說,都是可寫可不寫的。我把它們寫下來,主要因為中華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三報副刊主編向我拉稿。最近校閱書樣,重讀這兩輯的文章,自己還感滿意,更得向這些編輯先生女士們──蔡文甫、高信疆、弦、丘彥明──深深道謝。
第三輯?的四篇都是近三年的作品。其中一篇先由「人間」副刊獨家刊出,另三篇由香港「明報月刊」與「人間」(兩篇)、「聯副」(一篇)同時刊出,因此我更得向董橋、金恆煒這兩位主編道謝。小董近年來同我通信甚勤,憑他那幾封信,我認為他是當代最有才華學識的散文家之一,可惜他編輯事務太忙,平日寫文章的時間反而不多。恆煒每有信來,都稱我為「夏伯伯」,因為我同他先尊金溟若先生稱得上是患難之交。恆煒主編「人間」,成績斐然,十多年前我在臺北金宅同他初會面時,他還是高中學生。
前幾年,在字典上查看「雞窗」這一條,看到了晚唐詩人羅隱「雞窗夜靜開書卷」、南宋詩人范成大「雞窗夜可誦」這兩句詩(註),心?很高興,覺得將來出本散文集的話,倒可借用此二字為書題。「雞窗」即是書齋的代名,我生肖屬雞,差不多每晚二三點鐘「雞窗夜靜」之時,我不在讀書,即在寫文章、打字,而且往往清晨六點鐘才入睡,那正是古代農村社會雞鳴起床的時候了。在尚無電燈的時代,很少有人經常終宵不睡的。「雞窗夜可誦」情調的確不錯,但燈光不足,終夜讀書就太傷眼睛了,因之「雞窗集」這個書名古人還沒有用過(至少未見「四庫全書總目」)。清代倒有蔡澄這個人,著有「雞窗叢話」一小冊,寫下些人物掌故和讀書心得。此書已收入臺北廣文書局影印的「筆記續編」。古代大半讀書人,書根本讀得不多,也沒有什麼批評的頭腦,終其生往往只寫了一本筆記,一本「叢話」,情形是很可憐的。
我來美留學以前,還沒有女朋友。「紅樓生活誌」(原題「在北大教書的那一年」)只寫「日常生活」和「讀書生活」,未提「戀愛生活」,道理在此。進入中年後,在哥大教詞,每教到柳永那首「定風波」(自春來,慘綠愁紅……),感觸很多。柳永是文學史上最出名的風流人物,膩友特別多。此詞上闋寫男友走掉以後的一個女孩子,「終日厭厭倦梳裹。無那。恨薄情一去,音書無箇。」下闋女子自思,如能把柳永式的才子男友留住該多好:
早知恁麼,悔當初,不把雕鞍鎖。向雞窗,只與蠻牋象管,拘束教吟課。鎮相隨,莫拋躲,針線閒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陰虛過。
這個女孩子肯為自己的幸福打算,而且肚子?歪主意很多,人顯得非常聰明。電影「蝴蝶春夢」(The
Collector,威廉?偉勒導演)?有個神經病青年,愛上了一個女孩子,把她關起來,寸步不離她。女孩子綁劫男友的電影或小說我倒沒有看過。大學畢業後那幾年,我反正一天到晚在讀英詩,假如有「定風波」主角這樣聰明的女子愛上了我,把我關在她閨房?,「向雞窗,只與蠻牋象管,拘束教吟課」,我當然一點不會感到「拘束」,對她只有感恩的份。女的「鎮相隨,莫拋躲,針線閒拈伴伊坐」,這個境界很高,情調也美。唯一缺憾,想來柳永想像中的那位女郎,不認識多少字,只能「針線閒拈」相伴,當然比不上二人一起「吟課」,情形更理想。本書取名「雞窗集」,多少也嘲嘆自己僅憑讀書、看電影把「年少光陰虛過」的不智。
末了,我得向琦君姊、宋淇(林以亮)兄道謝。我那篇「歲除的哀傷」一九七八年正月在「華副」上發表後,琦君讀後感觸甚多,寫了一篇「海外學人生活的另一面──讀夏志清『歲除的哀傷』有感」,此文正好同我「自傳的片段」四篇配合,也就徵求琦君同意把她那篇收入本集。宋淇是濟安哥光華大學同學,同我來往已四十多年,稱得上是相交最深的摯友了。上海那幾年,宋淇有時下午來訪,濟安朋友較多,可能不在家,我總坐在沿窗書桌前讀書。臺港美國文友間,抗戰期間即同我在上海討論學問的就只有宋淇一人,因此也就不客氣請他為「雞窗集」寫篇序。
──紐約,一九八四,八月二十日
*註:羅隱句見「全唐詩」卷六百六十二「題袁溪張逸人所居」這首七律;范成大句見「石湖居士詩集」卷二十「嘲蚊四十韻」這首長詩。舊詩有時單句很有意思,兩行詩一起讀意境就較俗。羅隱「雞窗夜靜開書卷,魚檻春深展釣絲」這一聯,主要目的當然是拍張逸人的馬屁。「嘲蚊」寫實而不忘幽默,讀來比較有新意。該詩主要寫夏天蚊災之可怕。入秋以後,「虛空既清涼,家巷得寧輯」。因之男的可以讀書,女的可以織布:「雞窗夜可誦,蛩機曉猶織」。我童年在蘇州(范成大也是蘇州人),就沒有幾家人家自己織布了,石湖此聯讀起來也不夠親切。
稟賦.毅力.學問──讀夏志清「雞窗集」有感
林以亮
一
夏志清所有的中英文著作一向都由他自己寫序,甚至連同別人合作編譯的短篇小說集也不例外。他在學術界的經典之作:「中國古典小說」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屬「亞洲研究叢書」,也只不過由該叢書的總編輯寫篇簡介,而前言和洋洋灑灑的序文均由他本人執筆。原因是他對中西小說的知識淵博深邃,有時正文未盡欲言,只好利用長序來補充和發揮。袁枚「隨園詩話」有云:「傳字『人』旁加『專』,言人專則必傳也。」這句話可以應用在志清身上。他從英國文學入手,自詩歌而詩劇,而小說,更擴展到西洋文學、經典著作,然後轉折回來專攻中國古今小說,一面細讀,一面批注,數十年如一日。這一切努力再加上他扎實的學術基礎、一絲不苟的治學精神,和正統人文主義的文學批評家風度,使他成為研究中國小說的權威。別人可以和他持不同的評價和看法,為他寫序則非但吃力,而且不討好,因為有無從插手之苦。
志清之所以有今日的地位和成就,無非是他從中學起就孜孜不倦地追求知識和學問的必然結果。他雖然不乏良師益友,可是一向只埋首鑽研,從不依傍別人的門戶,獨來獨往,逐漸形成自己的主張和觀點。他並不是不熟悉「新批評」的方法,該派鼻祖勃羅克斯(Cleanth
Brooks)即他在耶魯時的業師,另三位大將也是他的老師。他不是對「結構派」一無所知,但不屑把自己局限於狹窄的範圍?,因為早已達到了更寬更高的境界。西洋文學的主流,大體上說來相當尊重個人的尊嚴和自由,也就是廣義的人文主義,文學批評自非例外。志清為學博大精深,當然是主流中的砥柱。他再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收了以儒家為主、以佛道為副的中心思想。在評論作家和文學作品時,他?重的不是技巧、象徵、神話等表面上的細節,而是作品深處的「感時憂國」和「悲天憫人」的人道精神。儘管他對「紅樓夢」有極高的評價,他仍不免喟嘆:「大觀園實在是多少小姐、丫鬟的集中營。」儘管他認為「金瓶梅」「把那時代『非人的』社會和家庭生活寫得透徹」,他卻引用了現代美國女作家Katherine
Anne
Porter的話:「『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描寫的生活無非是一連串灰暗單調的日子,偶然給一次性交所調劑。」然後指出:「如果這段描寫對勞倫斯的小說不太公平,大可用於『金瓶梅』上,當更為合適;可是西門慶一家所過的日子,非但沒有給經常出現的性慾上的火爆場面所調劑,反而變得更沉悶乏味。」在這一意義上說來,他繼承了十九世紀英國批評家安諾德的傳統。我們與其說是他是個職業批評家,不如說他是個文人(倒過來便是人文)批評家,他的地位絕不在現代美國學者兼批評家屈林、威爾遜等之下。他們都精通歐美國家的語言和文學,可是志清除了能閱讀德文、拉丁文、古英文、中世紀英文、古代冰島文之外,還融會貫通中西兩大文化,而這一點卻非一般西方學者或批評家所能企及。在這種情形之下,志清儼然成為漢學界的重鎮,因此下筆為文不得不分外謹慎。他說過:「看了一本我國小說名著,假如不想寫隨筆式的讀後感,就得參考至少二、三十種參考資料才能落筆成文。細讀一本小說,放進去的時間不多,參閱那些資料花的時間就多了。」這種工作是極費時間和精力的,加上他執教之外,同時受了盛名之累,登門求教者不乏其人,使他應付為難。近幾年來,儘管他仍兀兀治學,作品產量不免受到外務的影響而減少。這是朋友們私下覺得惋惜的。
前幾個月志清忽來信說,他計畫出一本新書「雞窗集」,囑我寫篇序:「我從不找人寫序,兄與弟相識最久,故有此請。……我們身後,一定有很多人撰文紀念我們,但自己讀不到,很可惜。不如生前看老友為我們寫的序,分享這份樂趣。」我閱信大吃一驚──人家說「受寵若驚」,我卻「受驚若寵」。當時的原始反應是:憑我的學識和功力,有什麼資格為志清的書寫序?然而他詞誠意懇,況且我們相識逾四十載,多年來他在美、我在港,極少聚晤,可是魚雁常通,也互相閱讀彼此的作品。他既然開口說生平沒有邀過人寫序,我又何忍推卻,只好硬?頭皮答應下來。好在素知他慢工出細活,且有一段日子可拖,並不急於一時。誰知最近九歌出版社蔡文甫兄已將「雞窗集」校樣寄來。細讀全書後,我深覺此約非踐不可,理由詳下。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我正在青島歇夏,華北眼看不保,奉父命趕去上海,誰知卻碰上「八.一三」。我和一位燕京同學商量這次是長期抗戰,不如往內地大學繼續學業,遂決定去南京轉漢口,向武漢大學登記借讀。誰知戰局情勢急轉直下,到了聖誕節,全校師生開始西遷,對我們借讀生並無特別安排,於是只好從廣州轉香港回上海租界內的大學借讀。一九三八年春,我們便入了光華大學英文系。那時同學中有來自中央大學哲學系的夏濟安,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柳存仁等,選的課教授好而學生少,彼此切磋,樂也融融。同學大都志趣相投,還合力出了一本同人雜誌:「文哲」,輪流編輯。我一向對有學問和有見解的人不惜傾心以交,於是課餘有暇到濟安家中閒聊,因此結識了志清。那時他大概比我們低兩三班,對哥哥頗為敬畏,我們談話時他默默旁聽,很少發表意見。(誰想像得到這寡言鮮笑的青年,日後竟會蛻變成一位說話如連珠砲的妙人!)畢業後不久濟安去了西南聯大,我就直接和志清交往。
我們學習的科目頗有近似的地方:二人都主修西洋文學,從英國詩歌入手,然後他轉攻中國小說,我轉攻中國詩詞。可是我的興趣太雜,當年醉心寫作,喜歡欣賞音樂、美術、芭蕾舞,為了家庭不得不經商,南遷後一度從事電影工作,一九六九年起方始回到學術界的崗位,遠不能同志清的專心致志相比擬。即以英國詩歌而論,他除了特萊頓(Dryden)和勃朗寧(Browning)之外,每位大詩人的全集都讀過,這是極少大學生做得到的。
我們都喜歡看電影,雖然出發點不同。志清是為了自娛,而我則由於職業上的需要。他的記性好,對電影的出品公司、上映年代、中文譯名、導演、主角等等,說來如數家珍。相形之下,我是為了工作而看電影,看得亂而雜,反而沒有他那麼專注而暢快。
我們都待過北平,但對平劇的認識不足,志清居留時間較暫,情有可原,我小時候常由聽差的帶去戲院看(非聽)戲,到了大學時代,主要興趣在西洋文學和藝術,對之不屑一顧。後從光華重回燕京,出入西郊城門不便,遂又失去大好機會。等到勝利後,開始發生興趣,為時已晚。生當平劇盛時,卻和志清一樣成為愛美的(amateur)「羊毛」,思之啞然失笑。
志清為程明琤的「海角、天涯、華夏」一書寫序,最後一節有這樣一段:
「亙古恆河」這篇文章,讀後不由我不想到很多問題,若沿?文思寫下去,本文就更不像一篇序了。但程明琤察訪各處的風土民俗、宗教儀式,自己也感想很多。我在序?把我的感想寫進去,可說是合乎她的筆調的。(見二○九頁)
閱後我忽然想起:何不採取同樣的手法替他寫序?這本散文集和志清其他的著作不同,並不是純學術性的,內容包括自傳、回憶和談書,正可以把我所知而書中未提起的部分寫出來作為補白,好讓讀者進一步了解作者的生平和治學之道。
二
「雞窗集」之名有其出典,唐羅隱有句云:
雞窗夜靜開書卷 真是一幅高士深夜讀書圖。窗下而能聞雞鳴,可知不止深宵,已近天明,雞鳴報曉了。柳永「定風波」一詞也有句「向雞窗」,是女子口吻,與本書不太切合。這書名很容易使人誤解,以為是隨筆性的文字,但是書中卻流露出作者讀書之勤、學問之博、見解之精,另外還有其辛酸的一面。第九十一至九十二頁有一段,我幾乎不忍抄:
今天元旦,有位主編從臺北打電話同我拜年,同時不忘催稿。拿出舊稿重讀一遍,覺得這次聖誕假期,更不如往年,更沒有時間做研究、寫文章。自珍即要六歲了,比起兩年前,並沒有多少進步。這幾天她日?睡,晚上起來,餵飽後,就要我馱她,一次一次馱下樓梯到樓門廊空地去玩。她騎在我肩上,非常開心,只苦了我,多少該做的事,永遠推動不了。馱她時當然不能戴眼鏡。昨夜大除夕,美國人守歲,少不了喝酒。有人喝醉了,在靠近大門前吐了一地,我看不清楚,滑了一交,虧得小孩未受驚嚇。二人摔交,我左掌最先?地,承受了二人的重量,疼痛不堪。虧得骨頭未斷,否則大除夕還得到醫院急診室去照X光、上石膏,更不是味道。我用功讀書,數十年如一日,想不到五、六年來,為了小孩,工作效率愈來愈差,撫摩微腫的左掌,更增添了歲除的哀傷。
相信任何人讀後都會心酸。自珍是志清的愛女,自幼身體不夠健全,到了晚上,腦波活動比白天活躍,非要父母輪流陪伴不可。志清在學校忙了一天之後,回家還要扮馬馱她以逗她開心,等她安睡後,才定下心來做學問,真是世上少有的「二十四孝父親」。要不是讀了他的心聲,我們怎麼會知道原來他在如此重大的壓力下讀書寫作?他自己還在慨嘆工作效率差,我們能不慚愧?
看了本書,我想起大學生涯一段小插曲。記得有一次去濟安家中,見案上有Francis Brett Young的小說:My Brother Jonathan,扉頁上題?涆o my dear brother Jonathan, from
T.A.荂CYoung那時是英國暢銷作家,當紅得令,工部局圖書館?他的小說我差不多已閱遍,只有這一冊沒有讀過,就老實不客氣向濟安借了來。只記得主角是個醫生,描寫他奮鬥求學成名的經過。扉頁上的題字使我納悶。志清難道有個英文名字,那麼濟安為什麼沒有?平時濟安一直稱呼他為志清,從未叫他Jonathan,會不會見到這本書,藉此替乃弟起一個英文名字?濟安的心思向來難以捉摸,當時沒有問,事隔多年,也就忘了。誰知「雞窗集」第八十六頁:「Jonathan(我的英文名字,只有外國朋友才這樣稱我)……」第五十八頁又有:「她(指教師Coleman女士)總規勸我:Jonathan,你心地這樣善良,靈魂這樣聖潔,能皈依主,多麼好呀!」看了之後,四十年前的疑團終於解開。可惜的是Young以後就漸漸為人淡忘,查閱近年的現代英國文學史,連他的名字都找不到了。
志清說過一句妙語:「我常常自嘲道,除了學術文章外,我寫的中文稿,不是序跋,就是悼文。」接到校樣時,我還以為本書可能例外,因為第一輯是「自傳的片段」,第二輯是「迷上電影也看戲」,等於回憶錄,想不到最後一輯「憶友談書」仍未能免俗;一篇介紹梁恆的「革命之子」;「江南風景,異國情調」是為程明琤的「海角、天涯、華夏」寫的序;「雜七搭八的聯想」是為吳魯芹「英美十六家」寫的序。「最後一聚」則是追悼我們的老朋友吳魯芹了。平心而論,志清治中國小說可以說具有全面的成就。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把有地位的中國新小說作家一一加以評估,獨排眾議,另立新論,當時被認為離經叛道的看法,現在已塵埃落下,成為定論。「中國古典小說」一書把六冊古典小說重新評定價值,更是經典之作。他私淑艾略特,艾認為每一個世紀應該出現一位大批評家,把英國大詩人的地位重新整理排列一下。志清是這方面的拓荒者,符合了艾的要求。以後的學者或許在某一冊小說上可以另有意見,加以補充,但恐怕很難超越他銳利洞徹的眼光和高瞻遠矚的氣魄。至於他撰寫專題論文如:「隋史遺文」、「鏡花緣」、「玉梨魂」各小說,也莫不鋒發韻流,將來彙集成書,當又是一部巨著。
志清幼年對中國舊小說並沒有深刻的認識。在第四十八頁上,他述及九歲讀小學三年級時,忽然發現了一套「三國演義」,就在暑假中把它讀完,以後再逢暑假又讀一遍,前後四遍。至於另一大堆林琴南的翻譯小說,則因冊數太多,放在原處,塵封不動。十一歲因「一二.八」戰事由蘇州遷居上海,不知從那?借來了「施公案」和「廣陵潮」,以「殺時間」的態度看完了,根本作夢也沒想到日後會以中國小說為主要研究對象。同一般青少年比起來,他的舊小說知識可以說是貧乏的。更奇怪的是那時他對五四運動以來出現的新小說家──一般中學、大學生的偶像如魯迅、茅盾、巴金、沈從文等──似乎從來沒有聽見過,連通俗小說家如張恨水等也毫無印象。但話說回來,這對他將來治學未始不是一個有利條件,因為靈臺空明,纖塵不染,猶如一面鏡子,可以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