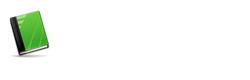他序1
我們在歷史轉軌的時節相遇天涯─寫在唐德剛《戰爭與愛情》再版之際
我們的朋友唐德剛走了。
他的一生,曾經參與同時也見證了上個世紀,在中國歷史上最風雲雷動,幾番掙扎幾番死生的時節,雖然他的大半生是在遙遠的異國度過,但他魂夢牽繞的還是那個容顏已老的故國。但凡在東方那塊土地上走出來的人,走向世界任何一個地方,誰不是這樣呢?特別是那些年,雖然生活在同一個時空的世界上,連至親的家人都彼此音訊渺茫,無從聞問。
也許是有這種共同的情懷吧?所以當時在美國的華人,總是多方打探來自故國的消息。我們在紐約的報社,自然就成了各方來打探訊息的對象,那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初期。
唐德剛教授所開啟的「口述歷史」記事,也給我們很大的啟發;在紐約華埠的華人,不但有百多年前乘豬仔船來美作勞工的先民後裔,並且還有曾幫助孫中山革命的協勝、致公兩個公所。老華僑們會告訴我們,在下城區華埠麥街那個小樓上,曾經是他們先祖和孫中山在此議事歇腳的地方,另外還有靠近布魯克林橋旁的一座舊樓上,有個衣館工會,阿叔給我看他們的資料,原來這些華工們在幾十年前,為了支持當時抗日的延安政權,他們籌資捐款不遺餘力。不幸到了美國執行麥卡錫政策之時,這些人竟被莫名其妙地打入牢獄,甚至有的家毀人亡……還有一些就是在國共內戰之時,從中國不同省分區域奔向海外的各個階層的難民,他們的臉上總是帶著失落和悽惶。我們從這些群落裡依稀可以讀到中國這百年來的縮影。
這時候華埠社區開始找資料,建檔案,而後終於成立了華埠歷史館和華工渡海紀念館。這是因為唐德剛教授「口述歷史」的啟發,大家開始注意歷史留下的軌跡。
也就在那時,因為美國剛從越南撤軍回來,由於反戰的聲浪四起,新的文化思潮出現了。當時的「嬉皮」風潮影響到文學、藝術、音樂、戲劇等各個領域,竟然形成了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文化運動。原是紐約下城區在二戰後廢置的幾十家破舊工廠,被各地湧來的藝文界人士改裝變造成畫廊、工作室、演藝廳及咖啡座等等,將原來就存在的藝術街格林威治村延伸至下面靠南的幾條街,就是蘇荷(SoHo)區。跟著世界各地的藝術家也紛紛進駐,大約十年光景,原來由世界藝術中心的巴黎,而逐漸轉移到紐約來了。
我們的報社就在蘇荷區旁邊,與小義大利區及華埠邊界。由於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影響逐漸擴及全美各地,諸如普普藝術、新寫實主義、後現代派、嘻哈風,甚至塗鴉風等等……這是資本主義首次接受挑戰的時刻,也是更多人對人類歷史進程走向這一時刻的反思;許多以前只專注於自己專業領域不食人間煙火的高級白領們,也開始主動或被動地走入人群,並且關心環境、集體等的關係。從不被注視的華人社區,這時候竟開始熱絡起來,竟有許多美國人也進入華埠,體驗不同族群的生活。
由於當時還是冷戰時期,國際間兩大不同意識型態的集團,互相詆毀謾罵,因而無從知道事實真相。我們的報社,是從各種不同渠道,冒著風險介紹了一些中國大陸情況,因而我們這裡就自然成了各路華人探詢的中心,甚至有從歐洲、東南亞及中南美洲各地來的華人同胞。
在蘇荷區裡也有許多華人藝術家的朋友,大家常在一家咖啡餐飲店會面,這裡聚集了四面八方的朋友。唐德剛教授因為完全沒有學究氣,他喜歡中國文學詩詞和戲曲、古董字畫等等,所以便和這些人也成了朋友。又由於他是較早來紐約的華人,他也沒有那些所謂的「偽洋鬼子」,張口閉口喜歡洋文成串美籍華人的派頭,所以華埠社區的老華僑們也和他有共同語言與文化鄉愁的交集(只是鄉音不同)。那許多年,他竟成了新舊華僑的朋友。
在離開故國幾千萬里之外天之涯的紐約,我們可以聽到老華僑們說他們祖輩坐豬仔船來做華工築鐵路的故事。在不同會所的阿叔們,會講支持中國抗日戰爭時的種種,以至於內戰時期流離失所奔赴來美的難民。也有那些家園破敗後,一個個不堪的惡夢般的人生……這裡竟成了華人在離亂世界裡,相濡以沫互相取暖的地方。
到了八十年代,大陸向外開放了。陸陸續續有許多人來美訪問、探親、交流。我們報社更忙了,各種不同的座談會,還要兼做人物專訪。其中也有一些是早年留美後又回國去參加建設國家的,幾乎每一個人都帶著滄桑與僕僕風塵回來了,回來重逢他們過去在美時的同窗或老友。大家都是兩鬢如霜,年華已老。相見恍如隔世。
我記得那年冬天的一個夜晚,我們大家聚在蘇荷那家我們經常聚會的餐廳裡。我們在傾聽一位唐德剛教授的朋友,六十年代前回國參加建設祖國的種種艱辛歷程,後來在文革中被認為是「美特」送到北大荒去勞改,說不盡的悽苦,漫漫長路……
我們在坐的每一個人都靜默著,沒有人說話。停了許久,他抬起頭來說:
「風霜經多了,反而鍛鍊了我們。那時全中國都苦啊,我們是一窮二白、老弱病殘的國家呀。同國家的命運相比,我們個人的這些也就不算什麼了……我們相信中國終會站起來的……」
真不知道以後的歷史,怎麼寫我們這個世代?在那個大風暴的時節,所有人感受的和看到的或許都不一樣吧?
那天我們談得很晚大家才分手。唐德剛教授因為家住在紐約市外的紐澤西州,他要趕車,得先走一會兒。我們看著他走出門去。外面正飄著雪,他向我們說再見。
那時雪花滿天,我們看見他的背影遠去,看見他招手彷彿是拂去飄下的雪花還是淚水?雪地上留下他一串腳印。
在那個史無前例的年代,我們共同走了過來。
唐德剛一生參與並見證了那個時代,他為我們留下一些記錄,這些見證也許可以給後人更多的啟示。總之,他走過去了,留下了腳印。
李藍
他序2
江山千萬里,家國四十年─為唐德剛著《戰爭與愛情》說緣起
唐德剛教授的長篇小說《昨夜夢魂中》就要結集出版了,由於這部作品曾經在我主編的文藝副刊上連載過,也許我比別人對這部小說之外的一些事知道得更多一些,所以他要我為這部小說再「畫蛇添足」一番,其實,作者的作品已經寫在那裡了,編者再說什麼都是多餘。我還是說點兒題外話吧。還得從認識唐德剛教授那年說起。
那還是一九七五年的時候,也是海外華人處在一個風雨激盪,為回歸和認同的問題而爭議徬徨的時候。當時《北美日報》的前身《星島日報》由我籌畫開闢了一個文藝版,在當時的美國僑社,這還是一個創舉,我們採取的編輯方針是以開放和認知的態度,也撇棄掉過去文化人「精神貴族」的思想情結。開闢不久即引起各方矚目,有的說我們思想進步,態度開明,為大家打開了一扇窗,讓人看到了另一片天地。但也有採否定態度的,認為我們反傳統,無端給我們扣上「左傾」的帽子,更無端地將我們的小報告打回去,把我們列在黑名單榜上。無故的騷擾和困惑就是故事裡必然的情節了。
這倒也給予我們極大的考驗;我們既然標榜開明和允許爭議,我們自己就得首當其衝做為人們的「試金石」,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終於慢慢地學會了如何寬容和愛人,如何打開心胸放眼世界,我們一點點地從自己的小圈子裡掙扎著走出來,走向群眾,走向世界。
就在這許多不同的反應中,我們接到了唐德剛教授的來信。他在信中說,二十多年前他們一群留美的文藝青年,當時也出版了刊物,組織了一個團體「白馬社」---至今他還津津樂道「當年白馬社如何,如何……」,可見對「白馬社」之深情。他說他擔心海外的文藝是否可以生長發芽?又懷疑我們是否能挨過兩年就要壽終正寢?但不管如何,他還是佩服我們有「烈士」的精神。當時我們編輯同仁還笑說,文藝版開始不久,放鞭炮的沒有,送花圈輓聯的倒來了;但也還是感謝他的關心,在十年前的那種光景,留學生來留學,多想學得一技之長,以安定謀生第一,誰去關心什麼中國文化的傳播?然而,我們也還是覺得感激,因為隔了千山萬水的家國,隔了遙遠的歲月之旅,竟還有人在關心著中國的文化在海外的播種。這給我們極大的鼓勵;不只是我們這批在台灣長大的中國人忽然認識到做為一個中國人的問題,也同時發現到,原來還有那麼多,那麼多遠從十年前,十五年前,二十年前,甚至更遠的三、四十年前,從中國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省分,經過各種不同的道路來到美國的中國人,也仍然還沒有忘記他們是黃河岸、長江邊上的炎黃子孫。那以後,我才知道唐德剛是胡適的得意門生,又是我的同鄉前輩安徽合肥人。他那時正在哥倫比亞大學做「口述歷史」---當時香港《明報》正在刊載他的《李宗仁傳》---就是口述歷史的成果之一。
時代的變遷和現實的生活,使我們這一代人變得較為自私倒是真的,很少聽到有人再談什麼理想、抱負或使命感這一類的話。「保釣運動」是一股熱流,使許多人忽然驚醒過來,認真地想到我們做為一個中國人的位置在哪裡?想到多年來我們在台灣唸書時所認識的「中國」,不過是教科書裡的文字和牆上的一張地圖罷了。三江、五嶽、黃河、長江、西安、洛陽,也無非是些美麗的名字而已。這使我們的「鄉愁」變得極為朦朧,如一齣舞台上的神話。那時候因為種種原因,當時的處境使我們無法一探大陸國土---唐教授序文裡已說到當時大陸尚未向外打開大門,而台灣已將我們護照吊銷,連親友通信都變得十分困難。我們那些懷抱著思國思鄉的遊子,常常跑到哈德遜河岸去觀水、觀船,潛意識裡想著什麼呢?或許有一天可以從這河出了海回去吧?或許盼望著有一天兩岸的親人都可以自由來往相聚吧?我坐在夕陽裡的石欄杆下,忽然想起在台灣的日子來,聽老一輩的朋友們談他們在大陸的家啊,大陸的那些故事,跑反啦、逃難啦、逃日本人啦,還有就是苦難裡的點點滴滴細緻的人情味,他們講不完地說著他們北方的家、南方的家、什麼紅高粱啦、紫蕎麥呀………,這使我們嫉妒而又羨慕他們有那麼多的「過去」---那過去就是他們和中國歷史的賡續連接。
唐德剛教授的「過去」,當然更叫我們羨嫉,他們經歷的那些年月,那些變遷,恰是中國從民國到邁向廿世紀裡一個天翻地覆的變化,而他自己的家庭背景,倒也像書中男主角一樣,是個龐大宅第和人口眾多的大觀園呢。他自己經過了抗日、國共內戰到負笈海外,真的像一折一折的戲在眼前經過。他做觀眾,他也做演員,什麼時代能夠給你這樣豐富的生活呢?
是十年之後。我到唐德剛教授的紐約市立大學「亞洲研究所」去拿這部長篇小說的續稿。他和我說到三十年前他們留美時的寂寥,說到他們當初辦刊物的熱情理想,也說到我們這一些背袱著中國文化傳統的美籍華人異國的飄零與落寞。「身在曹營,心在漢」,大概一直就是這些人的寫照,他還自我調侃說他們這種人是「熊貓」,因為稀有,有根深蒂固的中國文化傳統,又在美國西式文化的環境中待上了這麼多年,而仍然是「故國情長」。我們的下一代便沒有這種苦惱,因為他們已認同了這裡的文化。而年輕一代的留學生恐怕這種文化衝突感也沒有這麼深,因為他們生長的環境已開始西化了,他們也不那麼執著於自己文化的不可改變性。他們是較適意的一代,什麼風浪也沒經歷過,人生還如一張白紙。
就這十年的變化可真大,以前若在街上碰到一個黃皮膚的東方人,必定趨前探問是不是中國人?現在在紐約街上每天要不碰到一個東方人那才叫稀罕。大陸開放以後,留學生潮水一樣湧向各個城市和大學去,他們大概不會有我們、或更早的那些老留學生那樣的「鄉愁」了。就這個意義來看,我倒相信唐教授說他是「熊貓」的話,那背後是有許多悵惘的故事連接起來的。其實,那故事老早就在他心裡了,也許已經跟了他很多年,動機可能不單是他在序裡說的只是別人的故事那麼簡單,但凡在這個時代生活過來的中國人,誰在身上沒有幾個故事?而誰的故事裡,也都依稀可以辨識到自己的血淚辛酸影子。大時代就是一個無情的鐵輾子,它從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輾過去了,整體的命運尚且如此,何況個人?所以,我第一次聽完唐教授告訴我這個兩天之中以倒敘法寫下半個世紀變動的故事時,我認為這是誰的故事已無關宏旨,那是時代的寫照,中國人的故事。我當時極力慫恿他寫下來,是因為中國近半個世紀的動盪,他是親眼看見的,並且真真實實一路從那烽火裡、風雨裡、春花秋月裡僕僕風塵走了過來的,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不是單用數據寫歷史,因為人們向來不大相信史書的,中國歷代以來所謂史家如椽之筆,也不過是皇帝的御用罷了,倒不如民間詩人、文人的毛筆來得更能反映時代的真實面呢。不久,他認真寫起來了,第一次寄給我五萬字,以後是陸陸續續將續稿寄來的,一共約六十多萬字,連載了兩年。這其間,唐教授多次到大陸、台灣講學、開會、教課,又還給別的刊物寫稿,參加討論會,等等……,虧得他還記得小說裡的人物銜接,個性面貌,這部作品裡出場人物有四百多人,時間上從民國初年直到八十年代,空間上更橫越了美國與中國。無疑的,這是一部史書,一部社會的書。它從縱的面或橫的面,都給我們展示了一個歷史片段,而這個片段正是中國近大半個世紀以來最風雲變化騷動不定的時代,就宏觀的格局與微觀的細緻,中國的《紅樓夢》、日本的《源氏物語》都屬這一類。何況我們的歷史學家又是「紅學」專家,受《紅樓夢》的感染,是可以在整個氣勢上看得出來的。而這一段歷史,這些曾經在舊時代裡活躍著的人,也都將一個個走下歷史的舞台,再也不會復返了。不管你是抱著怎樣的心情看這些故事,這些人,這些事,也永遠不會在我們以後的時代再現。一個時代就這樣在紛紛攘攘中結束了。
由於這部人物眾多,舖排很大的小說是在報上逐日刊載的,喜歡追蹤情節的讀者自然不免失望。現在全書結集出版,讀者的情緒可以連貫下來,這種支離破碎感當可完全避免。在連載期中,就讀者的反應來說,許多與作者同時代走過來的人最有如同身受之感,特別是去年在紀念「七、七」抗日會上,曾有人大量影印小說中抗日戰爭中悲慘殘酷的一章分發給與會僑胞。大學裡一些研究近代史和社會學的學者們也都逐日剪存,作為史實保留。我相信,這些人已不單是以讀一部長篇小說來看待這部作品了。它更具有社會與歷史的意義在。
我們相信歷史學家的眼,往往像是用長鏡頭去看整個事件的發展和變遷的,他們可以站在高處看,站在遠處看。態度可以是冷漠而不動情。可是,當歷史學家自己就在時代裡面時,這鏡頭焦距是放在什麼位置呢?這些年來,不管是那裡的中國人,國內的也好,海外的也好,我們在行動上,在感情上也都隨著時代的大流經歷了一些事,甚至自己也在其中載浮載沉,跟著鬧鬨鬨走了一陣過場,我們各人回頭來看,又是什麼滋味呢?
我還記得在台灣那時候,夏天碰到颱風,大家張羅著儲水、存糧,等風來了,看風雨交加下徨徨奔馳的車陣人群,風把市招吹得七零八落,是一種人生的毀滅感、生活的倒置、命運的變數。人在這風雨裡抗爭著而又任命著。颱風的日子我們都經過了許多回,然而,往往那恐徨的騷動後又給人一種生存的慾望與勇氣。去年我從河西走廊經嘉峪關,走古絲道,越過舊時古都武威、張掖、酒泉,而抵敦煌。真正看到了「敕勒川」裡「天蒼蒼,野茫茫」的景象,宇宙洪荒,大野寂寥,像是開天闢地以來就是那樣地遼遂廣闊。車子一路行來,在大漠裡像一隻螞蟻般爬行。我們看到風捲起的野駱駝刺在戈壁上奔跑,遠山腳下,到處吹起了直上青雲的龍捲風,一直往上伸,往上伸,風的螺旋就像小貓在轉著圈子追逐著自己的尾巴。我從來不知道狂風怒號的另一種景象是這般可愛逗趣。可是不,當地人說,若果你不幸被捲入了那場風暴,黃沙蓋臉,日月無光,會把你吹得七顛八倒,直不起腰來的。看來世間事,大抵也是如此,怎麼看是大?怎麼看又是小?還許在你是站在什麼距離、什麼位置、什麼角度去看它。
我們的歷史學家在這部書裡,有時候是帶你在外面看,遠處看,但也帶你走進去看,血淚與辛酸,絲絲分明。在遠處看,或許是歷史;或許只是一齣戲。在裡面看呢,是苦難,也是人生。
這部小說現已由台灣遠流出版公司出版,書名改為《戰爭與愛情》。
李藍
一九八七年七月七日前夕
楔子
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實在是人類有史以來最文明的時代啊。你看那些野鴨野鵝,不是一陣陣地自天空飛下,向人們呱呱索食嗎?你不見那些自樹枝上下來的小松鼠,拱著手向人們討花生米吃!?幾千年來,它們都是人類「打獵」的對象啊!現在不都變成人類最好的朋友了嗎?
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實在也是人類有史以來最野蠻的時代啊。你會相信,那兒還有人把悶死的幼兒,在鍋裡蒸著吃?你會相信,有人死了,家人不敢葬,因為葬下去,可能被挨餓的飢民,偷去吃了呢?
我們生存在這個時代,實在是人類有史以來交通最發達的時代啊。「太空梭」的乘客,不是繞地球一圈,只需九十分鐘嗎?那飛到我們宇宙邊緣,萬萬里、萬萬里以外的衛星,它拍回來的照片,不是幾分鐘就可到達嗎?紐約的銀行家向日本東京匯款,撳一下電鈕,不是一秒鐘就可匯到嗎!?
但是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也是交通最閉塞的時代啊。它會使最不願分離的親人、情人,分散兩地,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從小到老、從紅顏到白髮;是生、是死、是酸、是苦……無音無信!
這世界真是這樣文明,又這樣殘酷嗎?這樣方便,又這樣閉塞嗎?是實人實事,還是虛構幻想呢?說是實人實事,知道的人或許嫌它不夠真實呢!不信的人也許會說那全屬虛構呢!是真?是實?是虛?是幻?---誰能作主?說它是真實,就真實下去吧;說它是虛構,也就虛構到底吧!有詩為證:
似真似假,
疑幻疑虛。
這是全國大演樣版戲的時代啊!
誰知戲台下面,也正分別演著
多少台,非樣版的真戲呢?
是戲劇?
是人生?
是國運?
是時代?
還是……?
朋友!
別再問了;
把它丟掉吧。雖然
丟不脫的,還有人人心頭,
永遠底創痕;
午夜醒來,環繞床邊,
永恆底黑影……
…………
話說---
代序
也是口述歷史
那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當美國尼克遜總統於一九七二年訪問了中國大陸之後,大陸上關了將近四分之一世紀的大門,對海外華僑迓然開了一條縫,我有幾位去國三十餘年的科學家朋友們,乃幸運地從這條縫裡擠了進去。那時我們一群還在牆外徘徊底逋逃漢,對他們是多麼羨慕啊!---那偉大的祖國河山;那童年所迷戀的溫暖家園;尤其是那慈愛的爹娘、歡樂嬉笑的兄弟姐妹、親人、朋友、伙伴……是多麼令人想念啊!我們焦急地等著聽他們回國探親的故事。
果然不久,他們就出來了。自祖國歸來的欷歔客中,有一位是我的總角之交,我知道他青少年時代的一切往事。他出來之後,我們日夜欷歔地談著他個人的見聞故事---這些故事太奇特,也太感人了。歷史上哪裡真有此事呢?小說家憑空編造,也很難幻想得出來!
我們細談之後,我這個搞「口述歷史」的老兵,乃想把他這份「口述」故事用英文記錄下來---那時的美國學者,訪問中國和越南出來的難民,曾是一時的風氣。口述者同意我的想法,但他的要求則是只要我不用「真名」「實地」,他所說的一切,我都可用中英雙語發表。可是這項工程相當大,我事忙,無法執筆,便拖了下來。
不久,我自己也拿到簽證,回國探親了。那還是「四人幫」時代。我個人的感受,和親見親聞的事實,想來我國歷史上的張騫、蘇武、班超、法顯、玄奘,乃至「薛平貴」的奇特經驗,也很難和我們相比。我住在北京的「華僑大廈」,和大廈中的旅客談來,我自己的經歷和去國時間算起來是最平凡而短促的了---我離開祖國才二十五年。雖然一旦還鄉連兄弟姐妹都不相識,但比起我的哭乾眼淚的朋友們來,我是小巫見大巫了---中華五千年歷史上,這個時代,對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國人,實在是太殘酷了。
我一入國門、初踏鄉土,立刻就想到美國作家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 1783-1859)筆下的李普萬溫柯(Rip Van Winkle)來,他在我的經驗中,竟成為事實。萬溫柯其人在美東克思琪山(Catskill
Mountains)中狩獵飲酒,忽然矇矇睡去,居然一睡二十年。醒來摸索還鄉,景物全非---好一場熟睡。我自己不意也狩獵醉臥於克思琪山下,一睡二十五年,始摸索還鄉,也是人事全非!---歐文幻想的「隨筆」(Sketch Book),竟成為我輩經驗中的事實!能不慨然。同時在我們底一睡二十五年期間,關掉大門的祖國之內所發生的種種故事,也真是匪夷所思---太奇特了,也太扣人心弦了。
在國內與老母弟妹一住兩個月,回想起在另一個世界裡二十五年的經驗---他們全不知道的經驗---也真如「南柯一夢」!
由於上述吾友的經驗,與我個人近半個世紀以來耳聞目睹之事,太奇特了,我想歷史書上是找不到的---雖然那些故事,和歷史上的故事也發生在同一段時間、同一個世界之上。它底「真實性」和「非真實性」,也和《資治通鑑》、《二十五史》沒有太大的軒輊。《二十五史》之中的「非真實性」還不是很大嘛。所不同者,史書必用真名實地,我要筆之於書,則格於老友要求,人名地名,都得換過。
再有不同者便是「史書」但寫舞台上的英雄人物,舞台下的小人物則「不見經傳」;但是真正的歷史,畢竟是不見經傳之人有意無意之中,集體製造出來的,他們的故事,歷史家亦有記錄下來的責任。
這個構想,時縈心懷。兩年多前,在一次文藝小聚時,我和那位呼我為「大兄」的編輯女作家李藍女士偶爾談起。她乃大加鼓勵,並允為我在紐約《北美日報》,她所主編的副刊「文藝廣場」上,加以連載。在她底堅決鼓勵之下,並蒙她上級諸友一再邀飲,我乃每天抽出了寫日記的時間,日寫三兩千乃至七八千字不等,由李藍逐日刊出。一發不可收拾,自一九八五年六月一日起,逐日連載達兩整年之久。為免脫期,有很多章節竟是在越洋飛機上寫的,由世界各地郵筒寄給李藍---這也算是個很奇特的撰稿經驗吧。
現在把這長至六十萬言的故事結束之後也不無感慨。它只為多難的近代中國,那些歷盡滄桑、受盡苦難的小人物們底噩夢,做點見證;為失去的社會、永不再來的事事物物,和慘烈的「抗戰」,留點痕跡罷了,他何敢言?
讀者們,知我罪我,就不敢自辯了。
唐德剛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六日於美國新澤西州北林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