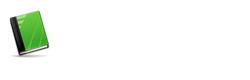一把金刀,一個褲襠祕密,
一樁又一樁的傳奇事蹟、街談巷語。
他,風流的好色之徒?人人喊打的漢奸?忠貞愛國的特務?
還是,救人無數的活菩薩?
熟悉麥家的讀者,可以看出《人生海海》與此前作品的關聯。他寫戰時情報人員詭秘的行徑、驚悚的冒險,可謂得心應手。但在新作中,麥家的野心不僅止於敘述一個傳奇人物而已,他同時著眼於發掘這一人物的前世與今生。……麥家善於講故事,以往諜報小說裡的布置——有如「風聲」的蜚長流短、「暗算」的背叛與被背叛、「解密」的懸而不解——仍然不缺,但爾虞我詐的戰場則融入日常生活中。──王德威
奇蹟、壯觀、魔法、魅力,甚至是鬼迷心竅。
正如本雅明所說的那樣,命運其實就是生者與罪過之間的關聯。
就古老村落而言,故事總是有空的,它一刻不停的看護著我們,為我們打發閒暇的時光,既為我們排憂解難又挑逗我們的好奇心,使我們沉迷於恐懼的焦慮之中。──程德培
本書特色
曾獲第三屆電視風雲盛典最佳編劇 、第七屆茅盾文學獎,《解密》、《暗算》、《風聲》作者最新力作。睽違九年,終於再見中國諜戰劇第一人精心寫就的現代奇譚!中國現代版的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譚)故事集!
屬於變動中國(抗日行動、國共内戰)的大時代裡,還原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的際遇。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麥家
當代著名作家,1964年生於浙江富陽。著有長篇小說《解密》《暗算》《風聲》等。《暗算》小說獲第七屆茅盾文學獎。作品被譯成30多種語言。《解密》《暗算》入選「企鵝經典」文庫,是迄今中國僅有的兩部收入該文庫的當代小說。2014年《解密》被英國《經濟學人》雜誌評為「全球年度十佳小說」,2015年獲美國CALA最佳圖書獎,2017年被英國《每日電訊報》列入「全球史上最佳20部間諜小說」。
麥家
當代著名作家,1964年生於浙江富陽。著有長篇小說《解密》《暗算》《風聲》等。《暗算》小說獲第七屆茅盾文學獎。作品被譯成30多種語言。《解密》《暗算》入選「企鵝經典」文庫,是迄今中國僅有的兩部收入該文庫的當代小說。2014年《解密》被英國《經濟學人》雜誌評為「全球年度十佳小說」,2015年獲美國CALA最佳圖書獎,2017年被英國《每日電訊報》列入「全球史上最佳20部間諜小說」。
目錄
推薦序
人生海海,傳奇不奇/王德威
「解密」的另一種途徑/程德培
第一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二部/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三部/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人生海海,傳奇不奇/王德威
「解密」的另一種途徑/程德培
第一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二部/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三部/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序
推薦序一
人生海海,傳奇不奇
王德威
麥家在中國大陸享有「諜戰小說之父」之名,在華語世界也廣受歡迎。他的作品如《解密》、《風聲》、《暗算》等描寫抗戰、國共鬥爭時期的諜報工作,波譎雲詭,極盡曲折複雜之能事,在當代文學裡獨樹一幟。也因此,麥家小說不僅被大量改編為影視作品,也早有多種翻譯版本問世。
以麥家受歡迎的程度,很可以如法炮製,以擅長的風格題材延續市場效應。但在頂峰之際,他卻突然收手,蟄伏八年之後方才推出《人生海海》。從書名看來,新作已然透露不同方向。麥家以往作品著眼一項機密訊息的傳遞破譯,一樁間諜遊戲的此消彼長,新作則放大視野,觀照更廣闊其實也更複雜的生命百態。麥家拒絕在舒適圈內重複自己,勇於尋求創新可能,當然有其風險,未來的動向如何,值得注意。
《人生海海》的書名對台灣、閩南地區的讀者而言應該覺得親切。這句俗語泛指生命顛簸起伏,一切好了的感觸;有種世事不過如斯的滄桑,也有種千帆過盡的釋然。麥家沿用這一辭彙,顯然心有慼慼焉。小說從民國延伸到新世紀,道盡大歷史的風雲變化,也融入了他個人的生命經驗。故事發生在浙東富陽山區,正是他的所來之處。
小說圍繞一個綽號為上校的人物展開,他出身浙東山村,因緣際會,從一個木匠入伍,自學成為軍醫,歷經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朝鮮戰爭,最後來到文化大革命。出入這些歷史場景,上校有了匪夷所思的冒險。他是出生入死的軍中大夫,也是風流無度的好色之徒;他曾當過和尚,更曾捲入諜報工作,周旋國共、日寇、漢奸集團之間。上校孑然一身,卻身分多變——他另一個外號竟是太監。而一切風風雨雨皆指向其下腹的刺字。那刺字寫些什麼?如何發生?何以成為人人希望一窺究竟的謎團?謎樣的上校或太監終於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遇巨大衝擊。
熟悉麥家的讀者,可以看出《人生海海》與此前作品的關聯。他寫戰時情報人員詭秘的行徑、驚悚的冒險,可謂得心應手。但在新作中,麥家的野心不僅止於敘述一個傳奇人物而已,他同時著眼於發掘這一人物的前世與今生。於是,上校的出身與之後回歸農村一一來到眼前,村中的四時變化、人事遭遇烘托出一段又一段的時代即景。這些描寫時以抒情韻味投射麥家的個人鄉愁,但卻更常凸顯一個南方鄉村的種種陰暗與閉塞。外面世界的天翻地覆與其說帶來村中的改變,不如說反照了改變的艱難。所有的矛盾與挫折在文革時爆發,首當其衝的正是像上校這樣歷經大風大浪,出走而又回返的人物。
這使全書的視景陡然放寬。麥家所關心的不僅是上校個人的遭遇,更是他與老少村民在閱歷和價值觀的劇烈差距。而雙方所付出的代價是慘烈的。麥家善於講故事,以往諜報小說裏的布置——有如《風聲》的蜚短流長、《暗算》的背叛與被背叛、《解密》的懸而不解——仍然不缺,但爾虞我詐的戰場則融入日常生活中。當大是大非的教條轉化為瑣碎的家常倫理,當堂而皇之的革命遭遇卑劣的人性時,一切變得如此黏滯曖昧,猶如魯迅所謂的「無物之陣」。
小說安排的敘事者是個少年,他的天真與苦悶恰恰與上校的神祕與世故形成對比。事實上,這位少年的成長和回顧才是小說的真正主軸。透過少年好奇的眼光,上校的一生逐漸浮出地表。就此,小說分為三部。第一部分交代上校在文革前後的背景和遭遇;第二部分則藉不同角色之口,倒敘上校早年傳奇;第三部分則跳接到當代,昔日的少年漂泊到西班牙,如今步入老境,回返故鄉,因為尋訪上校而發現更驚人的祕密。
細心的讀者不難理解麥家如何利用敘事方法,由故事引發故事,形成眾聲喧譁的結構。居於故事中心的上校始終沒有太多自我交代——他在文革中受盡迫害,最後其實是瘋了;反而是周遭人物的臆測、捏造、回憶、控訴、或懺悔層層疊疊,提醒我們真相的虛實難分。然而《人生海海》不是虛應故事的後設小說。麥家顯然想指出,寫了這麼多年的諜戰小說,他終於理解最難破譯的密碼不是別的,就是生活本身。
上校與少年來自同一山村,分屬兩代,命運極其不同,卻有出人意表的糾纏。麥家寫作一向精準細密,對這兩個人物的關係處理可見一斑。他們都是孤獨者,各自被「拋擲」到世界裡甚至世界外,由此展開生命之旅:上校投入戰爭與革命,歷經冒險與沉淪;少年偷渡前往馬德里,遭受無限的異國艱辛。比起來,上校的故事有諜報、有女色,還有縱欲、殺伐、情愛和背叛,而少年的故事則是一個海外遊子從無到有、資本主義式的創業寓言。但少年離鄉背井的原因又和他的家族與上校的恩怨息息相關。上校神祕的英雄氣質讓少年著迷不已,相形之下,少年在海外那些涕淚飄零的經驗反而是小巫見大巫了。多少年後,老「少年」還鄉,還是不忘故人;他必須挖掘上校最不可告人的祕密,以此完成上校的故事,以及自己(遲來的)成長儀式。在最奇特的意義上,他們成為不自覺的師徒。
《人生海海》前兩部分固然可觀,但真正讓讀者眼睛一亮的是第三部分。這一部裡,麥家的敘事速度突然加速,將少年與上校雙線情節合而為一,同時與上校背景一樣神祕的妻子林阿姨登場。這位女性是全書的關鍵人物,麥家筆下的她極其動人。經由她娓娓道來,上校的過去——他的風流往事、政治立場、婚姻關係,還有下腹的刺青……一一釐清——至此真相似乎大白。但上校本人早已智力退化如兒童,無從聞問了。故事急轉直下,聽完上校一生之謎最後的「解密」,老去的少年(還有麥家自己,以及理想的讀者)不得不喟然而退。
《人生海海》著力處理許多深沉的話題,善與惡、誘惑與背叛、屈辱與報復、罪與罰,此消彼長,載沉載浮。都說愛和時間能夠帶來寬宥和解,麥家也的確以此為小說添加正面色彩。但俱分進化,無有始終。愛或時間果然能證明或抹消生命的糾結麼?小說的敘述者何其有緣,認識了一位傳奇人物,但在講完/聽完上校的故事後,就像英國詩人柯勒立芝(Samuel Taylor Coleridge)《古舟子詠》(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裡的那個年輕人一樣,變得成熟了,卻再也走不出憂鬱。我們想到沈從文在《三個男人與一個女人》的一段話:
我老不安定,因為我常常要記起那些過去事情。一個人有一個人命運,我知道。有些過去的事情永遠咬著我的心,我說出來時,你們卻以為是個故事。沒有人能夠瞭解一個人生活裡被這種上百個故事壓住時,他用的是如何一種心情過日子。
麥家作品一向以傳奇取勝,《人生海海》高潮迭起,依然能滿足讀者期望。但我認為這部小說真正意圖是以傳奇始,以「不奇」終。「傳奇不奇」語出沈從文另一名篇之標題。所謂「不奇」,不在於故事吸引力的有無,而在於作家或敘事者從可驚可歎的情節人物裡,體悟出生命不得不如此的必然及惘然。這是人生的奧祕,還是常識?
《人生海海》的基調是幽暗的,小說的終局甚至鬼氣彌漫。而我以為這才是麥家作品從過去到現在的底色。他的諜報小說之所以如此動人心魄,因為寫出常人常情常理所不能、也不敢碰觸的祕密——絕對威脅也是絕對誘惑。他的人物在愛國或叛國的表面下,都散發一種頹廢耽溺的氣質,甚至忘我。上校的故事何嘗不也如此?《人生海海》試圖將這樣的感受擴大,作為回看故鄉甚至歷史的方法。危機是真實的,冒險是奇異的,真相是虛無的。如何將傳奇寫成不奇,這是很大的挑戰。據說這是麥家策劃寫故鄉的首部,他將如何講述未來的故事,令我們無限好奇。
推薦序二
「解密」的另一種途徑——讀麥家長篇《人生海海》
程德培
一
麥家因其《解密》和《暗算》而名揚天下。就其文類而言,被歸於「諜戰小說」一檔。其實在這些長篇之前,麥家也寫過不少中短篇,這些與「記憶」有關的作品被人稱之為「小人物系列」。《刀尖》之後,麥家曾表示要「抽身而去,開闢新的『陣地』」。這不,差不多十年過去了,我們等來了長篇新作《人生海海》。起先,我不懂「人生海海」何意,只是讀到小說最後一章才得知,這是「一句閩南話,是形容人生複雜多變,但不止這意思,它的意思像大海一樣寬廣,但總的說是教人好好活著而不是去死的意思。」小說的主旨和作者的追求變數由此可以想像。
《人生海海》試圖告別過去的「諜戰」、「特情」或「密碼」之類的稱謂,但要做到脫胎換骨談何容易。比如講故事,那可是麥家的立身之本。《人生海海》中,故事不止捲土重來,而且變本加厲。故事總是社群的生活,離鄉的奔波和返鄉的旅途總是其常見的形態,其中有著可以傳遞經驗的「忠告」,專注於無名的畏懼,關注於並不靠譜的閒話和傳說。於是,我們跟隨眾說紛紜的故事,來到了一個老式江南村落:一個前靠海龍山,後有老虎山的雙家村,那裡有著無盡無止的言說,「爺爺和老保長在祠堂門口享太陽,嚼舌頭。」就古老村落而言,故事總是有空的,總是在場,總是在身邊,它一刻不停的看護著我們,為我們打發閒暇的時光,既為我們排憂解難又挑逗我們的好奇心,使我們沉迷於恐懼的焦慮之中。於是,村裡的怪人怪事,上校的鬼屋及其傳說便隨風而至,隨聲而落。
記得麥家在談到《風聲》時曾說道:「為什麼我取名為《風聲》?風聲這個詞就蘊含著一些不確定性,「風聲」是指遠處傳來的消息,這個消息是真是假我不知道。從某種意義上說,歷史就像風聲一樣飄忽不定,真假難辨。至於誰的說法是真,你自己去判斷吧。所謂歷史就是一些不同的講述,我們永遠無法抵達它的真相。」這段話對《人生海海》來說依然有效。隨著太監之謎,上校傳奇的軍旅人生的降臨,我們的閱讀始終徘徊在尋找真相的旅途中。上校即太監,他無疑是小說的中心人物。就像古老的英雄傳奇陷於世俗的人云亦云,以訛傳訛的言辭,涉足於各種不同之人層疊交錯的講述一樣。奇怪的是,上校並不直接和我們照面,他也從自我講述和坦露心聲。他的故事、祕密和人生都是被爺爺說、老保長說、小瞎子說、阿姨說,以及那個敘事者的「我」說所包圍。《人生海海》充斥著不同的故事、傳說和猜疑想像,不同的人講的故事都是背面和側面,都是片段和碎片,故事一個接一個,東一個眼見,西一個耳聞,講有講者的情感判斷,聽有聽者的想法和闡釋。甚至每個人講故事的方式也不同,比如,「老保長講故事的樣式跟爺爺比,有兩多一少,多得是廢話和髒話,少的是具體年份」;而阿姨總「是一個表情:沒有表情的表情,波瀾不驚的樣子,一個腔調:風平浪靜落雪無聲的樣子,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腔調。」
上校作為一個完整形象的曲折人生,在無數的故事和傳說中逐漸成形並完成拼圖,而小說的敘述者「我」則在敘述中完成自己的成長故事。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是一部複調結構的作品,它是由說者和聽者共同完成的小說,它讓兩個陌生的人在絕對親近的地方中相遇。儘管他們的相遇總是陰差陽錯,當其中一個成熟長大時,另一個則心智尚未成熟;而當後者成熟長大時,前者則早已瘋癲,心智又回到了幼年。
二
解密的動力來自祕密,而圍繞祕密講故事一直是麥家難以擺脫的敘事衝動。太監之謎對少校而言是個不能揭示的祕密,為了保住祕密他「甘願當太監、當光棍、當罪犯」。圍繞著這個祕密,各種傳言、猜測、胡編亂造和確有實證的親眼目睹此起彼伏,時而洶湧,時而沉默,它構築著上校的人生傳奇和坎坷命運。當一個人不知道自己是誰的時候,自然而然也就會尋找他所歸屬的群體。莎士比亞提出過,「存在或不存在的問題。」普魯斯特則提出「屬於或不屬於」的問題,也就是歸屬問題。對於無法回答自己是誰的人,歸屬可以讓他找回意義、交流和存在。而現在為了守住這個祕密,回歸故鄉的上校,不僅身分成了問題,歸屬則更無法尋求。太監之稱成了閹割的焦慮,鬼子留下的髒東西成了恐懼的符號,成了眾人好奇之源,待解的密碼。他唯一相伴只是被人稱之為「活菩薩」的母親和那兩隻相依為命的貓。
上校的傳奇生涯成就了村落的故事之源。他是那麼的與眾不同,故鄉之人成了參與分享故事的局外人,而他呢,則是進入生活的被放逐者。上校既是英雄又是惡魔般的鬼怪之人,他既是聖人又是個「瘋子」或罪人,無論如何都是個有疑問、有祕密的人物。在一個隨波逐流和服從慣例的世界裡,這個人物的真實身分被淹沒;而在那個黑白顛倒的瘋狂歲月,真相成了個千古之謎成了奇談怪論。正如本雅明所說的那樣,命運其實就是生者與罪過之間的關聯。了解善與惡的命運,即通過惡來了解善的命運。一個時代誤解了另一個時代,一個卑鄙的時代用它自己的方式誤解了所有其他的時代。
太監之謎固然重要,圍繞著它的揭祕過程貫穿全書,也規定了敘事時間。但伴隨著揭祕的進程,我們也能感受到世態炎涼的「鬼氣」和時代變遷的暴力和張力。上校的故事是那麼動人,「有時間有地點有人物有事件,情節起伏,波波折折,聽起來津津有味,誘得蟋蟀都閉不攏嘴不叫,默默地流口水。」上校如此,其他人的故事又何嘗不是如此呢?比如直到第三部才登場的林阿姨那與上校愛恨情仇的故事,還有作為一個「民間思想家、哲學家、評論家,是我課外的同學和老師」的爺爺,因一時輕信的出賣行為,最終只能自殺身亡,包括那個大喇叭「老保長」的上海歷險等等。總之太監之謎發酵了一系列事件,它是一系列次生故事的創造者,它也同時成就講故事的一些要素:奇蹟、壯觀、魔法、魅力,甚至是鬼迷心竅。
隨著故事的進展,我們漸漸明白,太監之說的來由並非男人的那東西存在與否,相反,而是它特別的巨大,神奇到了可以成為軍統打入日偽內部的「利器」。問題出在了川島芳子刻在其小腹上的字,成為了上校終身的禁忌,如同真正的祕密一樣,它是不能大白於天下的。那些字形同閹割一般,讓上校過上了「太監」的生活,失去了男子的武功和無法收穫應當如期而至的愛情。儘管那碩大的陽具依然存在,但已名存實亡,成了令人害怕的東西。
總之,這個故事太曲折離奇,太匪夷所思。將一個與眾不同的英雄之奇特人生安放在太普通不過的村落,讓一個瘋狂的時代去撬動千年沉澱的道德倫理和良心底線,結果只能是不可思議。我們想要簡單地概括它或許是件冒險的事。雖然小說最終對敘事的疑點有所交代,對離奇之處有所解釋,特別是臨近結局抖露出太監之謎的全部真相,但對上校之悲劇性人生我們依然無法釋懷,對上校之命運所引起的困惑和茫然依然無法消除。太監之謎被解祕,但上校之人生命運還遠未解讀。作為人物形象,上校是離我們那麼遠,又那麼近。要理解自尊的幽暗和深不可測,要想安放一顆漂泊的心,我們或許還不如那兩隻與上校相依為命的黑貓白貓。
祕密的本質在於,無論如何也不能「揭示」它,就不能揭示它而言,它仍然是祕密。但祕密之所以吸引我們,就在於它催生了揭開它的欲望,這種欲望的持續正是敘事的時間。我們通常把祕密當作一種揭示,另一方面,也存在著一種真正的祕密,絕不能通過任何一種方式揭示出來。太監之謎似乎是解了,但少校的人生之謎依然存在,它以一種悲劇性的方式超越了我似曾相識的歷史階段,又以不同的方式暗算著我們各自的人生,以一種不完美的方式去想像一種完美。
三
雙重祕密突顯了上校不凡之處,這位出生時因胎位不正而大費周折來到了人世的奇才,「十七歲參軍,從打紅軍到打鬼子、打解放軍、打蔣介石、打美國佬,半輩子在前線戰場上」,他當過軍統,是位神槍手,更多的時間是一位天才的神奇軍醫,用林阿姨的話來說是「被他救過命的人也多了去」。殺戮與拯救構築了上校的英雄傳奇,也是其人生祕密的鎖和鑰匙。一方面,在昔日的背後隱藏著某種結構性的東西,它抗拒著我們;另一方面,一種結構化的東西又隱藏在我們自己的成見或現實意願裡,並決定著我們對他們投去的好奇目光。如何在失憶的世界裡,銘記鐫刻過往的歷史和事件,如何回溯社群在不同的時間點上受主流意識的侵襲、洗腦壓迫和支配性的創傷。「現在」總是驅逐著「過去」,並欲取而代之。「過去」總是有令人不安的熟悉的身影,死者總是令人揮之不去,悔恨不已又是一種暗自不斷的咬噬。恰如佛洛伊德在《一個幻覺的未來》中指出的:「生命,如同強加在我們身上的命運,對我們來說太過艱難,它為我們帶來太多的痛苦、失望,以及無法解的問題。」生命的要旨到底為何?曾被這個問題所縈繞的是宗教。它曾經如黑格爾所說,是享有保障的避難所,無此人類就無法去承受世界的茫然。但宗教死了以後,無論是被解放的人性之意識形態,還是掙脫了束縛的自然科學進步,卻沒有提供有效的替代物。對上校而言,生命的意義並不是契約通常總有一個終止的日子,而是誓約卻總是持續到死。
在一個極端瘋狂的年代中,上校的命運不是死亡就是發瘋。發瘋是死的另一種形式。於個人而言,選擇發瘋是避免永久的牢獄之災或槍斃,對敘事而言,發瘋才使得故事得以延續,唯其如此,麥家理想中的愛情故事才得以浮出水面。《人生海海》全書三部二十章一百節。到了第三部,時間好像洶湧澎湃,用迅猛的力量,將人和事快速推向各個方面。自從「我」逃之海外,經歷了各種磨難之後,分別以一九九○年代和二○一四年為回歸故鄉的兩個時間點,自身的情感故事和奮鬥史與上校的人生落幕和祕密的最終揭曉互為映襯、相互補充。就像小說中所提醒的,「我有兩個時間。我必須有兩個時間,因為我被切成兩半,一半在馬德里,一半在中國。我已經六十二歲……」,「我已經等了二十二年,每天用記憶抵抗漫無邊際的思念,用當牛作馬的辛勞編輯回來的夢。」
回鄉之路的講述古已有之。歷史上奧德賽是一個最終成功的受苦受難的形象,而正因為如此,他才遭到了柏拉圖主義者,但丁以及大多數蔑視「大團圓結局」的現代人之詬病和修正,認為他的漫遊就是可能的神聖完美的徵兆,而應該間接地看到「薛西弗斯的幸福生活」。「人生的意義不是對某個問題的解答,而是關於某種生活。它不是形而上的,而是倫理性的。它並不是脫離生活,相反,它使生命值得度過—也就是說,它使人生具有一種品質、深度、豐富性和強度。」我以為,特里,伊格爾頓這段回應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上校和「我」都經歷了回鄉,前者的傳奇成了一種祕密,而後者多少有點榮歸故里的味道;前者成就了人生的意義雖不乏悲劇性,後者雖經歷坎坷還是多少有點大團圓之嫌疑。不過「我」的還鄉確擔負著「視角」的功能,不但兩次返鄉完成了小說的結尾,而且故鄉的變化,從經濟發展污染到治理污染的變化雖有點浮光掠影,我們也是感同身受的。雖然,這段歷史離我們太近,無法以超然的態度重新講述,但由於這段歷史又經歷太多的變故,今天重溫似乎又覺得離我們太近,又很難身臨其境的覆述呈現其客觀性。相信麥家一定在書寫中能感受到其難度,但習慣在尖刀上行走又是其寫作的秉性,要其不寫還真不行。
《人生海海》的結尾依然承擔著解密的重任,太監之謎終於得到了揭示,小腹上所刻之字也終於在我的見證之下以修正的方式大白於天下。但這個天才是有限的,它局限於故事的天下,存活於說與聽的世界之內,誕生於某人在某種場合對一個側面的供述。隨著阿姨的最後陳述,隨著上校的妻子,「作為一個前麻醉師,阿姨以最為職業的方法結束了自己,追隨愛人而去」,一個淒美的愛情故事隨之誕生,差不多活了一個世紀的老人也終於離開了我們閱讀的視線。人究其實質而言就是我們關於他人的記憶。我們稱之為生命的東西,歸根結柢就是一張由他人的記憶編成的織錦。死之到來,這織錦便散開了,人們面對的便僅有一些偶然鬆散的片段、一些碎片。弗蘭克,克默德在《結尾的意義》中有一個著名的論斷:「結尾」是一個象徵著我們自己的死亡的形象,所以,它是可怕的,然而我們內心深處也有著對各種「可理解的結尾」的需求。雖然我們不願意面對自己的死亡,但對克默德來說,「結尾即是生命中的事實,也是想像中的事實。」太監之謎對雙家村的人來說,曾是眾口不一的傳說和猜測,面對有過部分共同經歷的見證者來說,又是部分的講述,不同側面迂迴的故事,《人生海海》不止是故事,還需要結構的組合。結構還是不同敘述的組織者,所以那個敘述者「我」的成長故事、海外經歷、「我」的所見所聞、「我」的說和聽或轉述才得以成為不可或缺的存在。可惜的是,那些曾經太想知道結尾的同村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共同的宿命過早地離開了我們,剩下的只是那一座座的墳地。爺爺、父親、母親與老保長、老瞎子都走了,他們都帶著各自的部分知曉,各自既同又異的認知方式,道德評判,甚至懺悔和各自的想像過早地離開了結尾。正像彼得,布魯克斯認為的,一切敘事「本質上都是訃告」,牠們的意義只有死後才能呈現。
四
麥家曾經說過,「我筆下的英雄都是悲劇性、不完美、不成功,沒有一個笑到最後的。」對此,小說家何大草這樣評述:「麥家的小說敘述到最後,幾乎都是走向毀滅。無論是N大學數學系高材生陳華南,還是陸家堰村目不識丁的瞎子阿炳,一個是破譯密碼的天才,一個是搞監聽的奇才,卻被自己的天才戕害了,如同一個用矛刺穿自己的盾。陳華南可以看得太遠,所以看不到腳下的陷阱;阿炳可以聽到最細微的天外之音、地下之聲,連帶也就聽到被欺騙的聲音。悲劇為什麼會發生?答案是一個死結。不然,怎麼叫做天才的悲劇呢?」
《人生海海》也寫英雄,但其處境已然不同。英雄的悲劇性書寫難以擺脫,但其生存的難處始終和時代的風浪休戚與共,隨普通人的「心靈法則」和「良知起伏」而波動。麥家的傳奇也不乏古怪的故事和人物譜寫的是一首英雄詩和愛的傳奇,它是既古老又那麼的現實,我們則在迷茫和困惑中被震撼了,一種難以理解的動人心肺縈繞著我們。即便我們要求助於隱喻和象徵也解決不了什麼問題。一位生命的嚮導卻被命運的悲劇烏雲所籠罩;一種既愛又恨的心理情感讓我們難以釋懷,菩薩心腸不離不棄但魔鬼般的惡卻又如影隨形;生與死可能容易分清,但要善惡分離卻沒那麼容易。傳奇人生是那麼的不同一般,可他的悲劇人生卻讓我們觸摸到了人人皆知的現實處境,包括腳踏實地的故土,清晰可辨的村落圖景,以及無法忘卻的瘋狂年代。
英雄詩為人格撰寫,人格外殼對我們是如此生死攸關,脫去它就要冒死亡或瘋狂的危險,這也是為什麼上校即使瘋癲也不忘記要抹去那刻在他小腹上的恥辱之字的原因所在。人格是抵抗絕望的神經性的防禦性機制,他無法承認真實的人之處境,無法忘記真正令人害怕的東西,他所經歷的死亡與再生,正如帕爾斯所說:「死而再生,談何容易」。「不容易」是因為,人身上需要死的東西是如此之多。上校的人生經歷無數的槍林彈雨,出手超越敵我的手術刀的人道搶救,經過失去自我的恐懼和堅不可摧人格的廝殺,囚禁與逃亡的輪替,瘋狂的重影互為替身的幻想等,經歷了九九八十一難,在愛神的眷顧下,那些恥辱之字「最終變成了一幅畫,一棵樹,褐色的樹幹粗壯,傘形的樹冠墨綠得發黑,垂掛著四盞紅燈籠」。具有象徵意義的是,上校唯一的遺產便是那套用金子打製的醫用手術刀具。
「我」終於講完了他的故事,當然也同時裹挾了「我」的成長史,曲折難忘的奮鬥史。麥家想通過這個複調式的故事來推進其小說的轉型和升級。效果如何?各人自有評說。我的感覺是,作者為此付出諸多努力,比如語言和結構,除了將你說,我說,他說的故事片段如何熔為一體之外,還有一個「報紙上說」不斷穿插全書,每每讀到這裡我都回想起自己走過的那些個歲月,那時什麼「教育」也沒有,除了「報紙上說」外還有什麼?還比如如何將奇人奇事納入當代生活的變化,如何借助故事的魅力拓展小說作為一種體裁所給予我們的幫助,那就是幫助我們理解人類生活的多樣性和我們自身道德的偶然性……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一個再了不起的作家也是人而不是神,某些與生俱來的才能要擺脫也難,就像那種近乎偏執的想像,又像對祕密和守護祕密的青睞等。想像或許是現實存在的反面圖像,一個被靈感震撼的世界,一種認識官能有機的相互作用,一種為意識與無意識相互滲透的解釋圖式或是一種急於表達的被剝奪的方式。有個作家認為,「偏執狂似的想像是一種反叛和脫離社會的特殊方式,但不僅如此,他還將它比作一種迷幻藥。他認為,它撕破了生活的陳腐而使人麻木的表層,使他接觸到某種更深刻和更豐富的,但不幸也可能是虛幻的事物。最為重要的是,它使他感到自己更充滿活力,有一種比官方的理性文化所敢於承認的更加強烈和絕對的自我。它是一種『震顫性譫妄,是思想犁鏵在震顫中填平畦溝』。它還近似於一種生存的強烈情感,這種情感是某些宗教經驗的特徵:『用水也能點燈的聖人,其記憶差錯代表上帝氣息的遠見卓識者,真正的偏執狂—對他來說,無論是在充滿歡樂還是藏有威脅的領域中,一切都在組織他自己的中心脈搏周圍……』」(〔美〕莫里斯,迪克斯坦著,方曉光譯,《伊甸園之門》,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一二五、一二六頁)這個作家便是平欽,他在為自己的想像力特徵所做的辯護時如是說。
《人生海海》講究複調,它經常讓兩股不同的敘述力量在那裡拉拉扯扯。麥家又是一個喜歡不斷反覆重寫自己作品的作家:《密碼》改寫了十年,《刀尖》寫於二○一一年,一直到二○一五年還在修訂。不知《人生海海》會不會改寫,如果會的話,不知將如何修訂?
人生海海,傳奇不奇
王德威
麥家在中國大陸享有「諜戰小說之父」之名,在華語世界也廣受歡迎。他的作品如《解密》、《風聲》、《暗算》等描寫抗戰、國共鬥爭時期的諜報工作,波譎雲詭,極盡曲折複雜之能事,在當代文學裡獨樹一幟。也因此,麥家小說不僅被大量改編為影視作品,也早有多種翻譯版本問世。
以麥家受歡迎的程度,很可以如法炮製,以擅長的風格題材延續市場效應。但在頂峰之際,他卻突然收手,蟄伏八年之後方才推出《人生海海》。從書名看來,新作已然透露不同方向。麥家以往作品著眼一項機密訊息的傳遞破譯,一樁間諜遊戲的此消彼長,新作則放大視野,觀照更廣闊其實也更複雜的生命百態。麥家拒絕在舒適圈內重複自己,勇於尋求創新可能,當然有其風險,未來的動向如何,值得注意。
《人生海海》的書名對台灣、閩南地區的讀者而言應該覺得親切。這句俗語泛指生命顛簸起伏,一切好了的感觸;有種世事不過如斯的滄桑,也有種千帆過盡的釋然。麥家沿用這一辭彙,顯然心有慼慼焉。小說從民國延伸到新世紀,道盡大歷史的風雲變化,也融入了他個人的生命經驗。故事發生在浙東富陽山區,正是他的所來之處。
小說圍繞一個綽號為上校的人物展開,他出身浙東山村,因緣際會,從一個木匠入伍,自學成為軍醫,歷經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朝鮮戰爭,最後來到文化大革命。出入這些歷史場景,上校有了匪夷所思的冒險。他是出生入死的軍中大夫,也是風流無度的好色之徒;他曾當過和尚,更曾捲入諜報工作,周旋國共、日寇、漢奸集團之間。上校孑然一身,卻身分多變——他另一個外號竟是太監。而一切風風雨雨皆指向其下腹的刺字。那刺字寫些什麼?如何發生?何以成為人人希望一窺究竟的謎團?謎樣的上校或太監終於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遇巨大衝擊。
熟悉麥家的讀者,可以看出《人生海海》與此前作品的關聯。他寫戰時情報人員詭秘的行徑、驚悚的冒險,可謂得心應手。但在新作中,麥家的野心不僅止於敘述一個傳奇人物而已,他同時著眼於發掘這一人物的前世與今生。於是,上校的出身與之後回歸農村一一來到眼前,村中的四時變化、人事遭遇烘托出一段又一段的時代即景。這些描寫時以抒情韻味投射麥家的個人鄉愁,但卻更常凸顯一個南方鄉村的種種陰暗與閉塞。外面世界的天翻地覆與其說帶來村中的改變,不如說反照了改變的艱難。所有的矛盾與挫折在文革時爆發,首當其衝的正是像上校這樣歷經大風大浪,出走而又回返的人物。
這使全書的視景陡然放寬。麥家所關心的不僅是上校個人的遭遇,更是他與老少村民在閱歷和價值觀的劇烈差距。而雙方所付出的代價是慘烈的。麥家善於講故事,以往諜報小說裏的布置——有如《風聲》的蜚短流長、《暗算》的背叛與被背叛、《解密》的懸而不解——仍然不缺,但爾虞我詐的戰場則融入日常生活中。當大是大非的教條轉化為瑣碎的家常倫理,當堂而皇之的革命遭遇卑劣的人性時,一切變得如此黏滯曖昧,猶如魯迅所謂的「無物之陣」。
小說安排的敘事者是個少年,他的天真與苦悶恰恰與上校的神祕與世故形成對比。事實上,這位少年的成長和回顧才是小說的真正主軸。透過少年好奇的眼光,上校的一生逐漸浮出地表。就此,小說分為三部。第一部分交代上校在文革前後的背景和遭遇;第二部分則藉不同角色之口,倒敘上校早年傳奇;第三部分則跳接到當代,昔日的少年漂泊到西班牙,如今步入老境,回返故鄉,因為尋訪上校而發現更驚人的祕密。
細心的讀者不難理解麥家如何利用敘事方法,由故事引發故事,形成眾聲喧譁的結構。居於故事中心的上校始終沒有太多自我交代——他在文革中受盡迫害,最後其實是瘋了;反而是周遭人物的臆測、捏造、回憶、控訴、或懺悔層層疊疊,提醒我們真相的虛實難分。然而《人生海海》不是虛應故事的後設小說。麥家顯然想指出,寫了這麼多年的諜戰小說,他終於理解最難破譯的密碼不是別的,就是生活本身。
上校與少年來自同一山村,分屬兩代,命運極其不同,卻有出人意表的糾纏。麥家寫作一向精準細密,對這兩個人物的關係處理可見一斑。他們都是孤獨者,各自被「拋擲」到世界裡甚至世界外,由此展開生命之旅:上校投入戰爭與革命,歷經冒險與沉淪;少年偷渡前往馬德里,遭受無限的異國艱辛。比起來,上校的故事有諜報、有女色,還有縱欲、殺伐、情愛和背叛,而少年的故事則是一個海外遊子從無到有、資本主義式的創業寓言。但少年離鄉背井的原因又和他的家族與上校的恩怨息息相關。上校神祕的英雄氣質讓少年著迷不已,相形之下,少年在海外那些涕淚飄零的經驗反而是小巫見大巫了。多少年後,老「少年」還鄉,還是不忘故人;他必須挖掘上校最不可告人的祕密,以此完成上校的故事,以及自己(遲來的)成長儀式。在最奇特的意義上,他們成為不自覺的師徒。
《人生海海》前兩部分固然可觀,但真正讓讀者眼睛一亮的是第三部分。這一部裡,麥家的敘事速度突然加速,將少年與上校雙線情節合而為一,同時與上校背景一樣神祕的妻子林阿姨登場。這位女性是全書的關鍵人物,麥家筆下的她極其動人。經由她娓娓道來,上校的過去——他的風流往事、政治立場、婚姻關係,還有下腹的刺青……一一釐清——至此真相似乎大白。但上校本人早已智力退化如兒童,無從聞問了。故事急轉直下,聽完上校一生之謎最後的「解密」,老去的少年(還有麥家自己,以及理想的讀者)不得不喟然而退。
《人生海海》著力處理許多深沉的話題,善與惡、誘惑與背叛、屈辱與報復、罪與罰,此消彼長,載沉載浮。都說愛和時間能夠帶來寬宥和解,麥家也的確以此為小說添加正面色彩。但俱分進化,無有始終。愛或時間果然能證明或抹消生命的糾結麼?小說的敘述者何其有緣,認識了一位傳奇人物,但在講完/聽完上校的故事後,就像英國詩人柯勒立芝(Samuel Taylor Coleridge)《古舟子詠》(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裡的那個年輕人一樣,變得成熟了,卻再也走不出憂鬱。我們想到沈從文在《三個男人與一個女人》的一段話:
我老不安定,因為我常常要記起那些過去事情。一個人有一個人命運,我知道。有些過去的事情永遠咬著我的心,我說出來時,你們卻以為是個故事。沒有人能夠瞭解一個人生活裡被這種上百個故事壓住時,他用的是如何一種心情過日子。
麥家作品一向以傳奇取勝,《人生海海》高潮迭起,依然能滿足讀者期望。但我認為這部小說真正意圖是以傳奇始,以「不奇」終。「傳奇不奇」語出沈從文另一名篇之標題。所謂「不奇」,不在於故事吸引力的有無,而在於作家或敘事者從可驚可歎的情節人物裡,體悟出生命不得不如此的必然及惘然。這是人生的奧祕,還是常識?
《人生海海》的基調是幽暗的,小說的終局甚至鬼氣彌漫。而我以為這才是麥家作品從過去到現在的底色。他的諜報小說之所以如此動人心魄,因為寫出常人常情常理所不能、也不敢碰觸的祕密——絕對威脅也是絕對誘惑。他的人物在愛國或叛國的表面下,都散發一種頹廢耽溺的氣質,甚至忘我。上校的故事何嘗不也如此?《人生海海》試圖將這樣的感受擴大,作為回看故鄉甚至歷史的方法。危機是真實的,冒險是奇異的,真相是虛無的。如何將傳奇寫成不奇,這是很大的挑戰。據說這是麥家策劃寫故鄉的首部,他將如何講述未來的故事,令我們無限好奇。
推薦序二
「解密」的另一種途徑——讀麥家長篇《人生海海》
程德培
一
麥家因其《解密》和《暗算》而名揚天下。就其文類而言,被歸於「諜戰小說」一檔。其實在這些長篇之前,麥家也寫過不少中短篇,這些與「記憶」有關的作品被人稱之為「小人物系列」。《刀尖》之後,麥家曾表示要「抽身而去,開闢新的『陣地』」。這不,差不多十年過去了,我們等來了長篇新作《人生海海》。起先,我不懂「人生海海」何意,只是讀到小說最後一章才得知,這是「一句閩南話,是形容人生複雜多變,但不止這意思,它的意思像大海一樣寬廣,但總的說是教人好好活著而不是去死的意思。」小說的主旨和作者的追求變數由此可以想像。
《人生海海》試圖告別過去的「諜戰」、「特情」或「密碼」之類的稱謂,但要做到脫胎換骨談何容易。比如講故事,那可是麥家的立身之本。《人生海海》中,故事不止捲土重來,而且變本加厲。故事總是社群的生活,離鄉的奔波和返鄉的旅途總是其常見的形態,其中有著可以傳遞經驗的「忠告」,專注於無名的畏懼,關注於並不靠譜的閒話和傳說。於是,我們跟隨眾說紛紜的故事,來到了一個老式江南村落:一個前靠海龍山,後有老虎山的雙家村,那裡有著無盡無止的言說,「爺爺和老保長在祠堂門口享太陽,嚼舌頭。」就古老村落而言,故事總是有空的,總是在場,總是在身邊,它一刻不停的看護著我們,為我們打發閒暇的時光,既為我們排憂解難又挑逗我們的好奇心,使我們沉迷於恐懼的焦慮之中。於是,村裡的怪人怪事,上校的鬼屋及其傳說便隨風而至,隨聲而落。
記得麥家在談到《風聲》時曾說道:「為什麼我取名為《風聲》?風聲這個詞就蘊含著一些不確定性,「風聲」是指遠處傳來的消息,這個消息是真是假我不知道。從某種意義上說,歷史就像風聲一樣飄忽不定,真假難辨。至於誰的說法是真,你自己去判斷吧。所謂歷史就是一些不同的講述,我們永遠無法抵達它的真相。」這段話對《人生海海》來說依然有效。隨著太監之謎,上校傳奇的軍旅人生的降臨,我們的閱讀始終徘徊在尋找真相的旅途中。上校即太監,他無疑是小說的中心人物。就像古老的英雄傳奇陷於世俗的人云亦云,以訛傳訛的言辭,涉足於各種不同之人層疊交錯的講述一樣。奇怪的是,上校並不直接和我們照面,他也從自我講述和坦露心聲。他的故事、祕密和人生都是被爺爺說、老保長說、小瞎子說、阿姨說,以及那個敘事者的「我」說所包圍。《人生海海》充斥著不同的故事、傳說和猜疑想像,不同的人講的故事都是背面和側面,都是片段和碎片,故事一個接一個,東一個眼見,西一個耳聞,講有講者的情感判斷,聽有聽者的想法和闡釋。甚至每個人講故事的方式也不同,比如,「老保長講故事的樣式跟爺爺比,有兩多一少,多得是廢話和髒話,少的是具體年份」;而阿姨總「是一個表情:沒有表情的表情,波瀾不驚的樣子,一個腔調:風平浪靜落雪無聲的樣子,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腔調。」
上校作為一個完整形象的曲折人生,在無數的故事和傳說中逐漸成形並完成拼圖,而小說的敘述者「我」則在敘述中完成自己的成長故事。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是一部複調結構的作品,它是由說者和聽者共同完成的小說,它讓兩個陌生的人在絕對親近的地方中相遇。儘管他們的相遇總是陰差陽錯,當其中一個成熟長大時,另一個則心智尚未成熟;而當後者成熟長大時,前者則早已瘋癲,心智又回到了幼年。
二
解密的動力來自祕密,而圍繞祕密講故事一直是麥家難以擺脫的敘事衝動。太監之謎對少校而言是個不能揭示的祕密,為了保住祕密他「甘願當太監、當光棍、當罪犯」。圍繞著這個祕密,各種傳言、猜測、胡編亂造和確有實證的親眼目睹此起彼伏,時而洶湧,時而沉默,它構築著上校的人生傳奇和坎坷命運。當一個人不知道自己是誰的時候,自然而然也就會尋找他所歸屬的群體。莎士比亞提出過,「存在或不存在的問題。」普魯斯特則提出「屬於或不屬於」的問題,也就是歸屬問題。對於無法回答自己是誰的人,歸屬可以讓他找回意義、交流和存在。而現在為了守住這個祕密,回歸故鄉的上校,不僅身分成了問題,歸屬則更無法尋求。太監之稱成了閹割的焦慮,鬼子留下的髒東西成了恐懼的符號,成了眾人好奇之源,待解的密碼。他唯一相伴只是被人稱之為「活菩薩」的母親和那兩隻相依為命的貓。
上校的傳奇生涯成就了村落的故事之源。他是那麼的與眾不同,故鄉之人成了參與分享故事的局外人,而他呢,則是進入生活的被放逐者。上校既是英雄又是惡魔般的鬼怪之人,他既是聖人又是個「瘋子」或罪人,無論如何都是個有疑問、有祕密的人物。在一個隨波逐流和服從慣例的世界裡,這個人物的真實身分被淹沒;而在那個黑白顛倒的瘋狂歲月,真相成了個千古之謎成了奇談怪論。正如本雅明所說的那樣,命運其實就是生者與罪過之間的關聯。了解善與惡的命運,即通過惡來了解善的命運。一個時代誤解了另一個時代,一個卑鄙的時代用它自己的方式誤解了所有其他的時代。
太監之謎固然重要,圍繞著它的揭祕過程貫穿全書,也規定了敘事時間。但伴隨著揭祕的進程,我們也能感受到世態炎涼的「鬼氣」和時代變遷的暴力和張力。上校的故事是那麼動人,「有時間有地點有人物有事件,情節起伏,波波折折,聽起來津津有味,誘得蟋蟀都閉不攏嘴不叫,默默地流口水。」上校如此,其他人的故事又何嘗不是如此呢?比如直到第三部才登場的林阿姨那與上校愛恨情仇的故事,還有作為一個「民間思想家、哲學家、評論家,是我課外的同學和老師」的爺爺,因一時輕信的出賣行為,最終只能自殺身亡,包括那個大喇叭「老保長」的上海歷險等等。總之太監之謎發酵了一系列事件,它是一系列次生故事的創造者,它也同時成就講故事的一些要素:奇蹟、壯觀、魔法、魅力,甚至是鬼迷心竅。
隨著故事的進展,我們漸漸明白,太監之說的來由並非男人的那東西存在與否,相反,而是它特別的巨大,神奇到了可以成為軍統打入日偽內部的「利器」。問題出在了川島芳子刻在其小腹上的字,成為了上校終身的禁忌,如同真正的祕密一樣,它是不能大白於天下的。那些字形同閹割一般,讓上校過上了「太監」的生活,失去了男子的武功和無法收穫應當如期而至的愛情。儘管那碩大的陽具依然存在,但已名存實亡,成了令人害怕的東西。
總之,這個故事太曲折離奇,太匪夷所思。將一個與眾不同的英雄之奇特人生安放在太普通不過的村落,讓一個瘋狂的時代去撬動千年沉澱的道德倫理和良心底線,結果只能是不可思議。我們想要簡單地概括它或許是件冒險的事。雖然小說最終對敘事的疑點有所交代,對離奇之處有所解釋,特別是臨近結局抖露出太監之謎的全部真相,但對上校之悲劇性人生我們依然無法釋懷,對上校之命運所引起的困惑和茫然依然無法消除。太監之謎被解祕,但上校之人生命運還遠未解讀。作為人物形象,上校是離我們那麼遠,又那麼近。要理解自尊的幽暗和深不可測,要想安放一顆漂泊的心,我們或許還不如那兩隻與上校相依為命的黑貓白貓。
祕密的本質在於,無論如何也不能「揭示」它,就不能揭示它而言,它仍然是祕密。但祕密之所以吸引我們,就在於它催生了揭開它的欲望,這種欲望的持續正是敘事的時間。我們通常把祕密當作一種揭示,另一方面,也存在著一種真正的祕密,絕不能通過任何一種方式揭示出來。太監之謎似乎是解了,但少校的人生之謎依然存在,它以一種悲劇性的方式超越了我似曾相識的歷史階段,又以不同的方式暗算著我們各自的人生,以一種不完美的方式去想像一種完美。
三
雙重祕密突顯了上校不凡之處,這位出生時因胎位不正而大費周折來到了人世的奇才,「十七歲參軍,從打紅軍到打鬼子、打解放軍、打蔣介石、打美國佬,半輩子在前線戰場上」,他當過軍統,是位神槍手,更多的時間是一位天才的神奇軍醫,用林阿姨的話來說是「被他救過命的人也多了去」。殺戮與拯救構築了上校的英雄傳奇,也是其人生祕密的鎖和鑰匙。一方面,在昔日的背後隱藏著某種結構性的東西,它抗拒著我們;另一方面,一種結構化的東西又隱藏在我們自己的成見或現實意願裡,並決定著我們對他們投去的好奇目光。如何在失憶的世界裡,銘記鐫刻過往的歷史和事件,如何回溯社群在不同的時間點上受主流意識的侵襲、洗腦壓迫和支配性的創傷。「現在」總是驅逐著「過去」,並欲取而代之。「過去」總是有令人不安的熟悉的身影,死者總是令人揮之不去,悔恨不已又是一種暗自不斷的咬噬。恰如佛洛伊德在《一個幻覺的未來》中指出的:「生命,如同強加在我們身上的命運,對我們來說太過艱難,它為我們帶來太多的痛苦、失望,以及無法解的問題。」生命的要旨到底為何?曾被這個問題所縈繞的是宗教。它曾經如黑格爾所說,是享有保障的避難所,無此人類就無法去承受世界的茫然。但宗教死了以後,無論是被解放的人性之意識形態,還是掙脫了束縛的自然科學進步,卻沒有提供有效的替代物。對上校而言,生命的意義並不是契約通常總有一個終止的日子,而是誓約卻總是持續到死。
在一個極端瘋狂的年代中,上校的命運不是死亡就是發瘋。發瘋是死的另一種形式。於個人而言,選擇發瘋是避免永久的牢獄之災或槍斃,對敘事而言,發瘋才使得故事得以延續,唯其如此,麥家理想中的愛情故事才得以浮出水面。《人生海海》全書三部二十章一百節。到了第三部,時間好像洶湧澎湃,用迅猛的力量,將人和事快速推向各個方面。自從「我」逃之海外,經歷了各種磨難之後,分別以一九九○年代和二○一四年為回歸故鄉的兩個時間點,自身的情感故事和奮鬥史與上校的人生落幕和祕密的最終揭曉互為映襯、相互補充。就像小說中所提醒的,「我有兩個時間。我必須有兩個時間,因為我被切成兩半,一半在馬德里,一半在中國。我已經六十二歲……」,「我已經等了二十二年,每天用記憶抵抗漫無邊際的思念,用當牛作馬的辛勞編輯回來的夢。」
回鄉之路的講述古已有之。歷史上奧德賽是一個最終成功的受苦受難的形象,而正因為如此,他才遭到了柏拉圖主義者,但丁以及大多數蔑視「大團圓結局」的現代人之詬病和修正,認為他的漫遊就是可能的神聖完美的徵兆,而應該間接地看到「薛西弗斯的幸福生活」。「人生的意義不是對某個問題的解答,而是關於某種生活。它不是形而上的,而是倫理性的。它並不是脫離生活,相反,它使生命值得度過—也就是說,它使人生具有一種品質、深度、豐富性和強度。」我以為,特里,伊格爾頓這段回應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上校和「我」都經歷了回鄉,前者的傳奇成了一種祕密,而後者多少有點榮歸故里的味道;前者成就了人生的意義雖不乏悲劇性,後者雖經歷坎坷還是多少有點大團圓之嫌疑。不過「我」的還鄉確擔負著「視角」的功能,不但兩次返鄉完成了小說的結尾,而且故鄉的變化,從經濟發展污染到治理污染的變化雖有點浮光掠影,我們也是感同身受的。雖然,這段歷史離我們太近,無法以超然的態度重新講述,但由於這段歷史又經歷太多的變故,今天重溫似乎又覺得離我們太近,又很難身臨其境的覆述呈現其客觀性。相信麥家一定在書寫中能感受到其難度,但習慣在尖刀上行走又是其寫作的秉性,要其不寫還真不行。
《人生海海》的結尾依然承擔著解密的重任,太監之謎終於得到了揭示,小腹上所刻之字也終於在我的見證之下以修正的方式大白於天下。但這個天才是有限的,它局限於故事的天下,存活於說與聽的世界之內,誕生於某人在某種場合對一個側面的供述。隨著阿姨的最後陳述,隨著上校的妻子,「作為一個前麻醉師,阿姨以最為職業的方法結束了自己,追隨愛人而去」,一個淒美的愛情故事隨之誕生,差不多活了一個世紀的老人也終於離開了我們閱讀的視線。人究其實質而言就是我們關於他人的記憶。我們稱之為生命的東西,歸根結柢就是一張由他人的記憶編成的織錦。死之到來,這織錦便散開了,人們面對的便僅有一些偶然鬆散的片段、一些碎片。弗蘭克,克默德在《結尾的意義》中有一個著名的論斷:「結尾」是一個象徵著我們自己的死亡的形象,所以,它是可怕的,然而我們內心深處也有著對各種「可理解的結尾」的需求。雖然我們不願意面對自己的死亡,但對克默德來說,「結尾即是生命中的事實,也是想像中的事實。」太監之謎對雙家村的人來說,曾是眾口不一的傳說和猜測,面對有過部分共同經歷的見證者來說,又是部分的講述,不同側面迂迴的故事,《人生海海》不止是故事,還需要結構的組合。結構還是不同敘述的組織者,所以那個敘述者「我」的成長故事、海外經歷、「我」的所見所聞、「我」的說和聽或轉述才得以成為不可或缺的存在。可惜的是,那些曾經太想知道結尾的同村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共同的宿命過早地離開了我們,剩下的只是那一座座的墳地。爺爺、父親、母親與老保長、老瞎子都走了,他們都帶著各自的部分知曉,各自既同又異的認知方式,道德評判,甚至懺悔和各自的想像過早地離開了結尾。正像彼得,布魯克斯認為的,一切敘事「本質上都是訃告」,牠們的意義只有死後才能呈現。
四
麥家曾經說過,「我筆下的英雄都是悲劇性、不完美、不成功,沒有一個笑到最後的。」對此,小說家何大草這樣評述:「麥家的小說敘述到最後,幾乎都是走向毀滅。無論是N大學數學系高材生陳華南,還是陸家堰村目不識丁的瞎子阿炳,一個是破譯密碼的天才,一個是搞監聽的奇才,卻被自己的天才戕害了,如同一個用矛刺穿自己的盾。陳華南可以看得太遠,所以看不到腳下的陷阱;阿炳可以聽到最細微的天外之音、地下之聲,連帶也就聽到被欺騙的聲音。悲劇為什麼會發生?答案是一個死結。不然,怎麼叫做天才的悲劇呢?」
《人生海海》也寫英雄,但其處境已然不同。英雄的悲劇性書寫難以擺脫,但其生存的難處始終和時代的風浪休戚與共,隨普通人的「心靈法則」和「良知起伏」而波動。麥家的傳奇也不乏古怪的故事和人物譜寫的是一首英雄詩和愛的傳奇,它是既古老又那麼的現實,我們則在迷茫和困惑中被震撼了,一種難以理解的動人心肺縈繞著我們。即便我們要求助於隱喻和象徵也解決不了什麼問題。一位生命的嚮導卻被命運的悲劇烏雲所籠罩;一種既愛又恨的心理情感讓我們難以釋懷,菩薩心腸不離不棄但魔鬼般的惡卻又如影隨形;生與死可能容易分清,但要善惡分離卻沒那麼容易。傳奇人生是那麼的不同一般,可他的悲劇人生卻讓我們觸摸到了人人皆知的現實處境,包括腳踏實地的故土,清晰可辨的村落圖景,以及無法忘卻的瘋狂年代。
英雄詩為人格撰寫,人格外殼對我們是如此生死攸關,脫去它就要冒死亡或瘋狂的危險,這也是為什麼上校即使瘋癲也不忘記要抹去那刻在他小腹上的恥辱之字的原因所在。人格是抵抗絕望的神經性的防禦性機制,他無法承認真實的人之處境,無法忘記真正令人害怕的東西,他所經歷的死亡與再生,正如帕爾斯所說:「死而再生,談何容易」。「不容易」是因為,人身上需要死的東西是如此之多。上校的人生經歷無數的槍林彈雨,出手超越敵我的手術刀的人道搶救,經過失去自我的恐懼和堅不可摧人格的廝殺,囚禁與逃亡的輪替,瘋狂的重影互為替身的幻想等,經歷了九九八十一難,在愛神的眷顧下,那些恥辱之字「最終變成了一幅畫,一棵樹,褐色的樹幹粗壯,傘形的樹冠墨綠得發黑,垂掛著四盞紅燈籠」。具有象徵意義的是,上校唯一的遺產便是那套用金子打製的醫用手術刀具。
「我」終於講完了他的故事,當然也同時裹挾了「我」的成長史,曲折難忘的奮鬥史。麥家想通過這個複調式的故事來推進其小說的轉型和升級。效果如何?各人自有評說。我的感覺是,作者為此付出諸多努力,比如語言和結構,除了將你說,我說,他說的故事片段如何熔為一體之外,還有一個「報紙上說」不斷穿插全書,每每讀到這裡我都回想起自己走過的那些個歲月,那時什麼「教育」也沒有,除了「報紙上說」外還有什麼?還比如如何將奇人奇事納入當代生活的變化,如何借助故事的魅力拓展小說作為一種體裁所給予我們的幫助,那就是幫助我們理解人類生活的多樣性和我們自身道德的偶然性……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一個再了不起的作家也是人而不是神,某些與生俱來的才能要擺脫也難,就像那種近乎偏執的想像,又像對祕密和守護祕密的青睞等。想像或許是現實存在的反面圖像,一個被靈感震撼的世界,一種認識官能有機的相互作用,一種為意識與無意識相互滲透的解釋圖式或是一種急於表達的被剝奪的方式。有個作家認為,「偏執狂似的想像是一種反叛和脫離社會的特殊方式,但不僅如此,他還將它比作一種迷幻藥。他認為,它撕破了生活的陳腐而使人麻木的表層,使他接觸到某種更深刻和更豐富的,但不幸也可能是虛幻的事物。最為重要的是,它使他感到自己更充滿活力,有一種比官方的理性文化所敢於承認的更加強烈和絕對的自我。它是一種『震顫性譫妄,是思想犁鏵在震顫中填平畦溝』。它還近似於一種生存的強烈情感,這種情感是某些宗教經驗的特徵:『用水也能點燈的聖人,其記憶差錯代表上帝氣息的遠見卓識者,真正的偏執狂—對他來說,無論是在充滿歡樂還是藏有威脅的領域中,一切都在組織他自己的中心脈搏周圍……』」(〔美〕莫里斯,迪克斯坦著,方曉光譯,《伊甸園之門》,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一二五、一二六頁)這個作家便是平欽,他在為自己的想像力特徵所做的辯護時如是說。
《人生海海》講究複調,它經常讓兩股不同的敘述力量在那裡拉拉扯扯。麥家又是一個喜歡不斷反覆重寫自己作品的作家:《密碼》改寫了十年,《刀尖》寫於二○一一年,一直到二○一五年還在修訂。不知《人生海海》會不會改寫,如果會的話,不知將如何修訂?
二○一九年三月三十日於上海
內容連載
第一部
第一章
一
1.
爺爺講,前山是龍變的,神龍見首不見尾,看不到邊,海一樣的,所以也叫海龍山;後山是從前山逃出來的一隻老虎,所以也叫老虎山。老虎有頭有頸,有腰背,有屁股,還有尾巴和一隻左前腳—因為它趴著在睡覺,所以光露出一隻。前山海一樣大,崇山峻嶺,像凝固的浪花,一浪趕一浪,波瀾壯闊。老虎翻山又越嶺,走了八輩子,一輩子一千年,累得要死,一逃出前山,跳過溪坎,脫險了,就趴下,睡大覺。這樣子,腦頭便是低落的,腰背是耷拉的,屁股是翹起的,尾巴是拖地的,並甩出來,三隻腳則收攏,盤在身子下。唯一那隻左前腳,倒是盡量支出來,和甩出來的尾巴合作,一前一後,鉗住村莊。
登上山頂—老虎屁股—往下看,村莊像被天空的腳蹄踏著,也像是被一聲口令聚攏起來,顯得緊密。其實是散亂的,屋子排的排靠的靠,大的大小的小,氣派的氣派破落的破落。這是一個老式的江南山村,靠山貼水,屋密人稠。屋多是兩層樓房,土木結構,粉牆黛瓦;山是青山,長滿毛竹和灌木雜樹;水是清水,一條闊溪,清澈見底,潭深流急,盛著山的力氣。溪水把鵝卵石刷得光滑,鋪在弄堂裡,被幾百年的腳板和車輪—獨輪車、腳踏車、拖拉機—磨得更光滑,有勁道。弄堂曲裡拐彎,好像處處是死路,其實又四通八達的,最後都通到祠堂。
祠堂威風凜凜,地主一樣霸占著村裡最闊綽的一塊空地和一棵大樹。樹是白果樹,也叫銀杏,樹幹粗得沒人抱得住,梢頭高過祠堂頂尖,喜鵲很安耽地在上面做窠、下蛋,生出下一代。春暖花開時節,嫩綠的葉苗像一支祕密部隊,從條紋狀的樹皮下鑽出,便一發不可收拾,發瘋似的向天空和枝椏爭搶地盤;要不了幾天,扇形的樹葉密密麻麻,隱起枝椏,遮天蔽日,擋風避雨,召集全村的麻雀都來過夜。秋末冬初,風是染料,把碧綠的樹葉子一層層染,最後染成黃銅色。一夜寒風,樹葉紛紛落地,鋪滿祠堂門前,蓋住青石板,跟著人的腳步混進周圍弄堂。弄堂沒規矩,卻總是深的,腸子一樣伸曲,寬的寬,窄的窄;寬的可以開拖拉機,窄的擠不過一副肩膀,只夠貓狗穿行。
春末秋初都是夏天,像夏天的凌晨四五點和夜晚七八點都是白天一樣。
第一章
一
1.
爺爺講,前山是龍變的,神龍見首不見尾,看不到邊,海一樣的,所以也叫海龍山;後山是從前山逃出來的一隻老虎,所以也叫老虎山。老虎有頭有頸,有腰背,有屁股,還有尾巴和一隻左前腳—因為它趴著在睡覺,所以光露出一隻。前山海一樣大,崇山峻嶺,像凝固的浪花,一浪趕一浪,波瀾壯闊。老虎翻山又越嶺,走了八輩子,一輩子一千年,累得要死,一逃出前山,跳過溪坎,脫險了,就趴下,睡大覺。這樣子,腦頭便是低落的,腰背是耷拉的,屁股是翹起的,尾巴是拖地的,並甩出來,三隻腳則收攏,盤在身子下。唯一那隻左前腳,倒是盡量支出來,和甩出來的尾巴合作,一前一後,鉗住村莊。
登上山頂—老虎屁股—往下看,村莊像被天空的腳蹄踏著,也像是被一聲口令聚攏起來,顯得緊密。其實是散亂的,屋子排的排靠的靠,大的大小的小,氣派的氣派破落的破落。這是一個老式的江南山村,靠山貼水,屋密人稠。屋多是兩層樓房,土木結構,粉牆黛瓦;山是青山,長滿毛竹和灌木雜樹;水是清水,一條闊溪,清澈見底,潭深流急,盛著山的力氣。溪水把鵝卵石刷得光滑,鋪在弄堂裡,被幾百年的腳板和車輪—獨輪車、腳踏車、拖拉機—磨得更光滑,有勁道。弄堂曲裡拐彎,好像處處是死路,其實又四通八達的,最後都通到祠堂。
祠堂威風凜凜,地主一樣霸占著村裡最闊綽的一塊空地和一棵大樹。樹是白果樹,也叫銀杏,樹幹粗得沒人抱得住,梢頭高過祠堂頂尖,喜鵲很安耽地在上面做窠、下蛋,生出下一代。春暖花開時節,嫩綠的葉苗像一支祕密部隊,從條紋狀的樹皮下鑽出,便一發不可收拾,發瘋似的向天空和枝椏爭搶地盤;要不了幾天,扇形的樹葉密密麻麻,隱起枝椏,遮天蔽日,擋風避雨,召集全村的麻雀都來過夜。秋末冬初,風是染料,把碧綠的樹葉子一層層染,最後染成黃銅色。一夜寒風,樹葉紛紛落地,鋪滿祠堂門前,蓋住青石板,跟著人的腳步混進周圍弄堂。弄堂沒規矩,卻總是深的,腸子一樣伸曲,寬的寬,窄的窄;寬的可以開拖拉機,窄的擠不過一副肩膀,只夠貓狗穿行。
春末秋初都是夏天,像夏天的凌晨四五點和夜晚七八點都是白天一樣。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二手書58折$208
-
二手書73折$262
-
新書79折$284
-
新書79折$284
-
新書79折$285
-
新書85折$306
-
新書9折$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