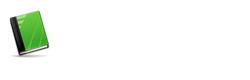推薦文
亦絢:
在很多地方讀《永別書》:與你所在之地隔一座小山的窗前,將睡的枕邊,打烊的辦公室,快速移動的高鐵上,老家已不屬於我的房間……讀到將近一半時,心跳得很快,我想我不能繼續下去,得喘口氣,在夜半像個鬼魂,摸黑點亮書房燈,找出《壞掉時候》和《最好的時光》──我必須把上游搞清楚。整個讀完《永別書》,我又取下《愛的不久時》,倚著枕頭,驚心動魄重讀一次。這迂迴的閱讀路線,有心人若跟著跑一遍,或許可以探出你小說裡幾個大主題的重複編織與變奏:家庭創傷、女性主義、同性戀(及其他)……但會否就不漏接《永別書》裡,由你輪番拋擲而來之物?我不確定。
乍讀《永別書》(尤其第一部),以為它是一本別開生面的啟蒙小說:關於愛情。雖你曾私下表示《愛的不久時》為典型「戀愛小說」,然而真正無法脫逃的,畢竟還是像〈幸福鬼屋〉的傾訴者與傾聽者;〈性愛故事〉的純青與黃鳳;〈在灰燼的夏天裡〉的許幼棉與賈心媛;來到《永別書》,賀殷殷和小朱。章憾文為《最好的時光》作序時,曾爬梳台灣同女小說脈絡──《永別書》著無庸議是「女同性戀」小說,不過書中人物之鮮明,心理地景之立體,又讓我感覺它能不只屬於同女,而剝除了性別,像十四歲的賀殷殷竭耗心神求得的一悟:「基本的人性」。除了女性情欲、姊妹情誼、女研社文化,在愛情的支線上,它更廣泛寫出了人在感情裡可能的殘忍和容忍,屏息讀著那些流淌過皮膚表面的高溫情感熔漿,使人隱隱想起某些久遠之事,那或是獨屬於青春的。也正因其感情與關係,「在人世間是稀罕的」,小朱被殷殷勉強說成「初戀」,其實是孤獨者一起孤獨?啟蒙同時也是(開)啟盟(誓),無論守約或背棄都是艱難,為使痛苦的水位下降,得用盡多少努力,才能獲贈那忽然記憶強度減弱的「完美時刻」,在那之前,「記憶的別無選擇,是人生的最高刑罰。」但我不能忽略的還有,賀殷殷關鍵的發問:「那些我們打算忘掉的事,我們曾經──一度以正確的方法,記得過嗎?」萬一我們將自己置入的,是一座假牢獄,該怎麼辦?這是小說中,特別提出「當定義想要推翻某些記憶時,我總不讓記憶倒下」的原因?但為何她有此把握?
就像,相較於小朱這段強悍的「原型」或「天敵」戀愛,書中鋪陳了另一段為時較長的伴侶關係:賀殷殷和何萱瑄。兩人在生活中相伴跳格子,直到非關背叛的謊言,病毒般覆蓋了殷殷的記憶體──假記憶真實地覆蓋掉了真實。她們原本可以繼續走下去的吧,賀殷殷疑似有過日子的本事,只要她願意「犧牲掉直覺,犧牲掉神奇時刻」,忍受「在關係中長期的孤單感」?但是我對萱瑄沒信心(沒有讚美誰貶抑誰的意思)。
比較好奇的是,書中著墨最多的兩段愛情╱關係,都因賀殷殷特出的書寫能力,而有了微妙變形:殷殷和小朱,兩人競賽誰能將對方變成「讀者」;殷殷和萱瑄,則較量彼此「想成為作家的欲望」。何以如此?究竟,作家身分的「光環」是什麼?才華這份禮物,又為何令人如此垂涎?竟使愛情關係,因摻入「寫作者身分」而有巨大變數?
還有一個不太重要的好奇:賀殷殷「意義非凡」的木頭盒子裡,收藏的電影票是哪幾部電影啊?
梓評
別後通訊:在揮手的時間裡
孫梓評╱張亦絢
★
梓評,
《永別書》並不真的太關切作家的光環或才華。必須比較回到表意弱勢族群所身受的剝奪感,也就是歷史性的巨大壓迫問題。所以也可以外延到其他身分或是無聲者的書寫危機上。無論小朱、萱瑄或殷殷,在表面錯誤不義行為背後,都存在一種(同志)生存掙扎與對出路的思考。她們都是以各自的出發點,在「憂國」的。「製造」出一個(或多個)寫女同志的作家,完全不同於單純的文學成就獲得,而牽涉到延續同志命脈的(象徵性)問題。如果只看她們彼此的衝突與背叛,不看她們事實上的相互援引與支撐,這是不完整的。殷殷扮演的當然是一個克服者的角色,也就是克服小朱對她的「責備」或者萱瑄的「力有未逮」,雖然這過程不無殘忍。但是從保存(同志)創造力這一事上來看,這三人是有隱形教練與同隊選手,既敵對(教練作為敵人是有其必要的)又庇護的共生關係的。所以不厭其煩地寫她們的「勾心鬥角」,為的不是說誰好誰壞,而是誰都出過一份力。小說對她們每一個代表的力量,都是肯定與否定兼有。因為這是我看到的,同志的多重奮鬥。愛情反而成為犧牲品,甚至祭品,這是悲劇的一面,但這也是另一種同志生命,一般比較看不到。無論是不當的壓力(小朱)或是扭曲的示範(萱瑄),從賀殷殷的角度,她看到的仍然是有意義的表達,而不是純粹的失敗,這是她可以做為回收者╱克服者的原因。這與相信作者天分的傳統,有很大的距離。誰能寫?不是有能力的人,是惦記著其他人力量與缺陷(圖改善)的那個(繼承)人。但是惦記者也不是一個鏟頭,人家要她怎樣就怎樣,她也要知道防衛與抉擇。她有其底線。
所謂漏接的問題,我想將無以計數。有次我問十歲的大姪子,你投球前要不要做暗號?他是一個非常純真的小孩,他馬上反問我:「我要做什麼暗號?我只會投直球而已。」《永別書》卻是沒有直球的。而且我以為「接不到」此事,本身就被我考慮做為衝擊感性的手段。懂得人會懂(接不到所要發動的各種體認),要罵我的人,去找我大姪子玩直球好了。倒也不是說我刻意要弄一個很難的球路,而是有作品是遷就讀者的,也有作品是遷就作品的。而且說回來,我可是都有打暗號的。還有,什麼上游下游。我雖不反對有人要把我其他的作品串起來讀,但對我來說,它們還是各自獨立,可以背對背跳舞的東西。先寫到這。還有不要亂問問題啦,電影票?我哪知道?其他所有問題,小說裡都有提示呀,不要假裝沒接到啦。這樣很好笑耶。
亦絢
★
亦絢:
小說家的「體貼」與「周到」,果然使小說人物心裡「有風景,還有暴風雨」。我喜歡你說她們三人有其「共生」,那麼除了「我們或許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殺死過別人一些」,或也因此激活原本可能怠弱的惰金屬吧。確實她們是「憂國」的,「我們受歧視而不懼、我們被隱形卻瀟灑,因為我們,深深為我們的真實不欺而自豪,我們是有信念的,不是嗎?那是我們的現代意義──」這是賀殷殷遭遇兩次「爆炸」後,猶然鏗鏘的發言。
前信說,讀此書「不能繼續下去,得喘口氣」,你必然毫不意外。我想這應也是多數人讀取「痛苦的神童」滔滔追憶後,會有的反應──你借我的小書《當影子成形時》,裡頭一篇〈成人身上的悲傷兒童〉,篇名簡直就是賀殷殷的鏡照:三歲被政治狂熱的父親性侵,承受巨量接觸的記憶暴力,同時,長於不倫家庭的母親並未伸出援手,反澆灌以冷言冷語。這些眼熟的片段,自〈淫人妻女〉可見端倪。你曾表示「被褻者」的主題是你特別關心並反覆思索的。這主題,在《永別書》有了極度細膩且完整的呈現(儘管賀殷殷已自行刪去一萬多字關於亂倫的敘述)。我在腦中蒐想一回,賀殷殷事事極端的原生家庭(當然不能忘記加上邀請她參加雜交未果的妹妹小惠),應是我讀過描寫家族的小說中,最「恐怖」的。(「兒童自覺不幸」!)
記憶一如閱讀。二讀、三讀,或讀一本別人畫了線的書,都不可能與初讀的空白狀態相同(不過就像書中說,從沒有一個記憶是單獨的,閱讀大概也是)。但書寫本身,卻可能寫在一張已被寫過的紙上而不自知。殷殷也曾擁有三年無染的童樨時光,那或許是記憶的白紙狀態;但她的寫,卻如同她的血,各種墨水加諸其中:你在小說中詳細建構殷殷外省父親所從來,更擴延出她客家母親相形複雜的二房身世,書中且有一些篇幅去寫改嫁的阿嬤、似有強暴嫌疑的外公、閩南人但受日本教育的外婆等角色;甚至還一度藉著《烏來鄉泰雅族耆老口述歷史》及攝影書所錄照片,試圖翻轉殷殷對自己血緣的認知。這張「被咀咒的家族」人物表,除了某種程度解釋了賀殷殷如何行走於形而上的無人曠野,繼而踏上女同之路,亦讓父母形象與性格更形立體,同時,這一切也和殷殷長久以來無所遁逃的「台灣」與台灣歷史,綁連、纏縛愈深。
我喜歡《永別書》採取一種私密傾訴、議論清晰,但又伺機迂迴的方式(讀時常想起你的專欄「我注意」),說一說就繞開、又看似不經意再提起。那其實更近於記憶本質,或說,人生本質。人生不像小說家想要在小說裡裁剪的那般工整。
「寫」,不僅僅是殷殷、小朱、萱瑄永恆的角力,它也讓我想起賀殷殷好險長成一個文學少女而非(如父親所灌溉的)政治少女,書中一段非常美的告白:
「小說是我的信仰。從小就是。我把自己奉獻給它,因為它曾把我從人世最險惡的欺騙(亂倫)中解救出來。不是因為我相信小說句句屬實,而是我知道──這門藝術,不是給予真實,而是以獨特的手段,傳授給人們,在乎真實的能力。」
正因為在乎真實,殷殷在第二次「爆炸」後遭遇巨大之毀,而企圖消滅所有經歷過的特殊記憶──然而她是這樣說的,「我也曾經在非自願的狀況下,被迫喪失我最珍愛的能力:我的記性。」「記憶,或許是我最擅長的事情了。」書末甚至透露,有些記憶,已經漸形斑駁、色淡。
埃及國王達姆斯與發明字母系統的神明托特會面,對托特說:你發明之物乃有助於遺忘,而非記憶。由此,我不免也懷疑賀殷殷如此辛苦將一切鉅細記下,雖是為了她所冀想的「倒塌學」,但難道不也因這些記憶正被迫(或自願)風化?
在一篇訪談稿中,讀到你用一句話形容自己:「我這一生都在持續抗拒消失的欲望。」不知為何,我首先想到的是「取消」(好吧其實我先想到的是,「好悲傷喔!」),彷彿字面上所談的消失,不是delete功能,是訂位人員在你本來的欄位上用原子筆打了一個大大的叉。與消失欲望相反的,大概(亦)即是書寫?
賀殷殷沿途留下麵包屑(她和「處處誌之」的武陵人,肯定不是用同一種材料當記號)。我偷偷撿了一些,邊吃邊數算賀殷殷年紀:她上國小,美麗島事件;她上國中,民進黨成立。疑似與你年紀相仿。為什麼你決定讓「賀殷殷」與「張亦絢」這樣密切靠近呢?這與你偏愛的「融化邊界」有關?《永別書》裡,「我」一直在對「你」說話。那個「你」是誰?書名有個副標題,「在我不在的時代」(讀完書,對「時代」二字有了嶄新體會)──那個「我」,是賀殷殷,還是張亦絢?如果是賀殷殷,她是真的「不在」嗎?
梓評
★
梓評,
哇喔,好高興看到你寫到埃及那段,那本是我為了《永別書》抄過的筆記一段!(來握手吧)後來因為「剪不進來」,就不費勁剪了。不過那是我思考這本書時的關鍵。它實在是很嚴厲又複雜的。就是說,記憶的工具如書寫,反而會削弱人本身做為記憶工具的能力。在小說裡,我之所以透過賀殷殷之眼,命名所有的「破爛記憶」,讓它與「漂亮記憶」對立,甚至強調「破爛記憶」的文化意義──既書寫,但又表達反書寫壟斷,除了有我對台灣歷史的反省,另一指導靈確實來自埃及。
還有就是,我從經驗知道,書寫有種委託不在場人記憶的功能,真的會使書寫者本身進入奇特的遺忘。這使得我在一校時,進入極度荒謬的狀態:啊?這樣的句子她也寫得出來?啊?這麼難寫的東西,要是我,我就寫不出來!(驚慌失措)作者太可笑了!(掩面)理論上,我當然知道我是這本小說的作者(這應該不會錯才是,不然就成科幻風了XD),但是在知覺上,那幾乎是另一個宇宙了。在剛寫完時,我會有一種我設定達成十分,但是最後,接受我得分只有九,然後因為那掉了的一分,不停傷心的狀態。但是我現在已經歸零了,與零分相較,就變成在開心,我有九分耶!至於你說的「不能繼續下去」,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意外,我知道預備給讀者的旅程並非坦途,但是如果讀者崩潰,我抄夏宇的歌詞給各位備用:已經有過幾次崩潰╱未來應該會平順許多……。
真有人膽大到要問,賀殷殷和張亦絢的關係!用算年紀地……,那很多六年級人口都可以算進來耶,好啦,不鬧你。好好回答呢(這真難……),總之這對我來說,不是個問題。比起演反派就在路上被打的演員,我只能說,這是職業的悲喜劇。如果是演員,我不會是那種,選擇要演新石器時代的獨眼男人,以便證明我有演技的演員。我很喜歡的一部關錦鵬的電影,曾經教我一件重要的事:最難演的,就是與自己最相似的角色。為什麼這樣靠近?因為我很勇於挑戰嘛。(完全厚臉皮地自吹自擂)然而坦白說,誰會那麼執著在你這個問題上呢?假使一個埃及人在讀,他或她,會很計較這種推測的相似性嗎?從另一面來說,演員演出的角色,就不是演員的生命嗎?融化邊界,這也是很好的理論,我滿捍衛的;不過如果是交換寫作者間的心得來說,在賀殷殷與張亦絢兩者之間,我分得很清楚。這個分別很重要。而且是我要負責領版稅。另一個最大的差別就是,你問不到賀殷殷問題,但是張亦絢得傷腦筋。或者說,在非文字的表達裡,比如遊戲,在戰亂中小孩發明的遊戲,與和平區小孩的遊戲,就可以看出差異……;如果小說是遊戲,一定要逆推,為什麼作者玩這樣的遊戲?的確可以「知影」一些什麼……。這是我不直接的回答,但不知是否讓你滿意。(以及讓所有蠢蠢欲動於這個問題的人滿意……)
超喜歡你說打叉那部份。「取消」就是取與消。
一板一眼的回答:副標的「我」當然是賀殷殷;這裡的「不在」,指的是賀殷殷在與大歷史同步時,自動或被迫隱形的一切──當然也可以有其他詮釋。所以她是真的「不在」。然後我也不知道「你」是誰。也許賀殷殷知道。──張亦絢(不得已)代答。亦絢
★
亦絢:
我沒忘記你是「文本派」擁護者──私以為以「張亦絢」所在座標,做為「賀殷殷」的定錨點,有一個重要的好處,如書中所寫,「七年級的絕不會像我們六年級的那樣記得戒嚴,但四五年級的,你知道嗎?我覺得,他們又記得太牢了」。身體的戒嚴記憶和解嚴記憶比例不過分懸殊地共存,應該也與這書的某些主題暗中扣合?
即是,《永別書》不僅是一冊女性成長小說、教人讀出冷汗的家族書寫,依書中所給的種種暗示,它還是一本屬於台灣的國族寓言。殷殷有一段這樣的說話:
在濫情一點的時刻,我會在心裡說:誰會比我對這個島的命運,更感興趣呢?它的被欺凌、被強灌人造記憶,使它受苦於「難以連貫成一個自我」而發聲。拼湊國格,如我從被亂倫的劫後餘生中,抵抗所有奪去我真實的努力,我和它,我們都是無奈卻堅決的縫補之人。沒有它歷史中「反抗內在殖民」那句話的砥礪,我這一生,不知會少掉多少勇氣、多少語言。──雖如此,這樣的話,我從不會去說它。有些東西,不用說的。
從歷史的角度重新看待「亂倫」、「不倫」,與台灣身世的對照感就更形強烈了。我僭越的閱讀是:
這個父,是台灣曾所屬的中國,但他亂倫,他「接收」了台灣。
這個母,是(未覺醒的)台灣主體性,她有著不倫之父,那不明的日本遺風既教養了母親的貴族氣(現代化),亦使她對於一個混沌成形中的「台灣」(流著一半外省血的女兒),竟是無法愛,或,不知道怎麼愛。(未覺醒的)台灣主體性,帶著自己也不清楚的傷痕,書中對母親有一段凌厲的評語:──那是比被殖民更沒有政治性、更無力、更卑賤、更難翻身──。╱以活屍形態立身的──「更被殖民者」。
賀殷殷認為母親「一輩子都抓緊那個『絕對無辜者』的感受」,這自然與殷殷所企圖的戰鬥是大相逕庭的。書中安排殷殷父親發狂般要小惠攻擊母親(「去幹你媽!」),其後,殷殷與母親有這樣的對話:「妳爸道過歉了,不要再追究。」「道過歉了?哪有?」「帶妳們去餐館吃飯就是道歉。」母親且補充道:「妳爸千錯萬錯,但妳不能否認,他對我們這個家庭的經濟有貢獻。」
那「道歉」,不知為何,讓人想起國民黨統治者向二二八及白色恐怖時代政治受難者的道歉。而國民政府建設、發展台灣的說法,大概也就是「對我們這個家庭的經濟有貢獻」吧──莫怪乎賀殷殷語重心長的一句:「將功贖罪最危險。」
故,這廿餘萬字砌成╱推毀的「我是誰」,某種程度,也在為台灣代言?
最核心的悲傷,可能是賀殷殷的永無歸屬感:女人也好,女同性戀也好;台灣人不台灣人,「沒有一個,是我真正屬於的族類──」
台灣航在浩翰蔚藍海上,或也有類似歎息。
讓我們回到賀殷殷的性。
殷殷所經歷的亂倫,「更加冷酷持久的,是它對記憶一事的摧殘。」但那並不表示,出了問題的只有「記憶」。如果一切傷痕都是從如同「強迫性的毒品灌食」般的「性」開始,要修復傷痕(可能嗎?)或使傷口得以暫時結痂,還是得回到「性」。
「從我有記憶以來,我就從不放鬆掉自己對性的注意力。」因為殷殷認為,「我必須把這部份假裝得夠好,才能證明,那個小孩──她沒有被擊倒。」同時,「只要我一閃神,殺掉那個小孩的慾望,就會凌駕一切事物之上。」
甚至,僅僅是親密的男孩同儕將手覆在她發燒的額上,就碰痛了一本活生生的亂倫史。
此處引了一段《挪威的森林》,殷殷擔憂自己:「不要成為直子那樣的女孩,導致木漉自殺身亡──」木漉,在日文原版,並沒有給出名字的漢字寫法。村上使用的是キズキ(KIZUKI)。念著這名字,常忍不住想到KIZU(傷)、KIZUNA(絆),後者指的是情感的牽繫。木漉死後,直子和渡邊有過一次濡濕的性交,那時他們「共有死者」;直子死後,渡邊和玲子姊也有過一次親密淋漓的性交,那時他們也「共有死者」。
「所謂性,那是內心的內心。」
「在性最純粹的一面上,它只有兩個問題:真正想要的是什麼?真正想給的是什麼?」
經歷兩次「爆炸」的賀殷殷,選擇出走,並展開「性的夏令營」,終站是維也納,遇見盧和凱洛玲,彼二人的「共有死者」是從小一起長大的摯友湯瑪斯。殷殷和他們,在對著彼此開敞的缺口中,注入誠實,三人完成了最好的性。
如果說,經過諸多壞毀,「性」還能修復,或許,真正需要的,是一個如愛麗絲.米勒所稱的「知情見證者」──在「偏心的陪伴」中,給出理解。而非企圖以「愛」解套(當然也不會是「床上的佈道家」),因為,「寬恕從來沒有療癒的效果。」
我很高興在賀殷殷列舉的人生關鍵時間點,除了兩次「爆炸」,沒錯過這項:「33歲,維也納。布列塔尼亞。」殷殷且前往湯瑪斯位於布列塔尼亞的家,拜會他的母親,她守護傷痕,她知情見證。
讀了又讀的《永別書》終於還是要結束了。我真的會將這本書忘得一乾二淨嗎?「永別」,既是賀殷殷從書頁中伸出的一次揮手,像小說最末,「我把你留在這裡」──老實說,我隱隱感覺,那也是你的一次揮手,你把「賀殷殷」留在這裡,你要去做(寫)別的事(小說)了。我猜對了嗎?
梓評
★
梓評,
初初寫出,你就讀得如此深入,驚訝之餘,我真是太感動了。
不得不收起我比較皮的那一面,認真討論。就分享一下《永別書》的方法吧。這個方法在寫作之前我並不知道,是一邊寫一邊發展出來的。我自己覺得,讀者如果以「釋義」的方式讀,一定會很辛苦,而且一定會發現,什麼象徵什麼這種模式,當多納入一個訊息或情節,模式似乎又不成立。以你提出來的部份來說,解讀賀殷殷父親如是,又會難以納入他反國民黨與認同本土民主的性質。至於「更被殖民者」,小說中賀殷殷的態度不是批評,反而是肯認,這不是說「更被殖民」是好事,而是願意指認痛苦,不用立場去架空它。那一段,在小說原時間段是在描述賀殷殷母親,但看到後來,就會知道,那也是賀殷殷在說她自己。因為亂倫倖存者,也是性殖民的見證。在台灣,「被殖民」這事,始終不夠以接受被殖民者本身處境的複雜度去對待。總是有惡劣的指導跑出來。不過在這裡我不深入談,只談方法。
我的態度是,人物與事件都是完整獨立的,小說裡的每一線,彼此可以參照,但從未給予「以A喻B」這種階層或從屬關係。不會把什麼當象徵處理,處理的反而是「一旦象徵就容不下的東西」。如果把A與B平行看,會產生C感想;這是企圖,但這對照同時不是結緊與設死的;當D線又參照進來,又會有因A+B+C+D產生的E感想。如果以絲線比,在時間的尺度上,A在一分鐘時可能是點綴,兩分鐘時給出可見形物,三分鐘時化為陪襯的布景,五分鐘後它又成為兩分鐘之形的反形。以一種時間萬花筒的方式在進行。而我的準則始終是,一切都「沒有代表性,但是要有參考性」。
把這個方法跟你說到的「國族寓言」併看,我更傾向說它是「國族欲言」;設計的是一整套的退化與退行,在這裡說「死外省人」是OK的,「歷史讓人頭痛」也是OK的;這種「退」,自然也是「以退為進」。如果說「代言」,應該不太是「代言」,而是「帶言」。因為我關心的是語言的可能性,而不是完好的論述。當然,整個「對經濟有貢獻」那段,你已經得到你的萬花筒,轉出的形狀,比我預想得還要豐富。小說根本不用將類比排列出來,某些情節與話語就會(即使它們相隔許多個章節)自動共振,讀者其實不用太推算作者要說得是什麼,要說深意是沒有什麼深意的。但是讀者感到的各式共振,在那多變的共振上所浮現的屬於各自的交響,那確實是比文字定位在書本位置之外,《永別書》真正的所在。小說的工作,只在編製各種可能的小樂器:小樹葉或小水杯,使風過時,響╱想起來。賀殷殷「性的困難」,是在某個程度較被完整呈現的,但它的作用同時也在框出一個領域:殷殷冒著自殺危險而知道她的性創傷之所由,其他所有人,包括床上的佈道家或所有致傷者(令人難以理解的性犯罪者),他們的慢性或急性瘋狂是從哪裡來的?賀殷殷後來幾乎成為她最初最反對的人,「只剩下性」。但她同時又是幸運的,我想我們都會有點為她高興。
最後,你要拐我是不成的;我根本沒在小說中出現呀。我照顧的是整部小說。最後一句話是殷殷對讀者說的,她功成身退了。揮手是我很喜歡的意象喔,竟然被你說出來了。我覺得人會揮手是很美麗奇特的一件事。手揮個不停,是為永別,是為書。沒有什麼猜不猜,但你總是有些對的啦。
亦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