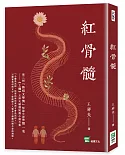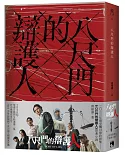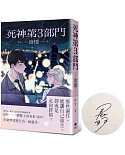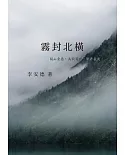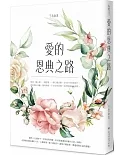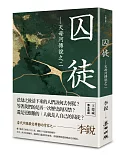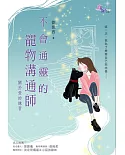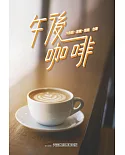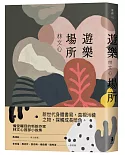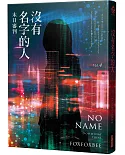追尋記憶中的烏托邦 ——周桂音談《月光的隱喻》
問:請問故事的靈感來自何處?
答: 我一直想寫一個關於溫室的故事。大學時期,我經常幻想著一幅城市風景:灰色的城市一角,有個溫室。這個溫室在陰冷的城市中微微發亮,裡面有城市失去的所有東西。城市和我們現今身處的城市有一點像,卻又有點不一樣。它們的樣貌以零散的段落出現在我隨意塗寫的零星紙片上。
大學畢業後,我搬到永和,一面補習法語一面四處打工。永和貸居處是一間老舊的頂樓加蓋小屋,若爬上屋頂,便能看見大片北縣風景:層層疊疊的鐵皮屋頂,擁擠的馬路,新店溪對岸的公館一角。站在七層樓高的鐵皮屋頂上,看著喧囂的車水馬龍,因著難以言喻的情緒而動容。我突然發覺,多年來幻想描繪的灰色城市,和我剛上大學時看見的台北很有關聯。站在永和的屋頂上,很想對這樣的風景訴說些什麼,便動手寫起醞釀已久的溫室故事。
問:小說發生的時間是在戰後的世界,為何對這樣的世界有興趣?
答:其實一開始並沒有設定特殊的時空背景,只想在一個中立的空間,述說一個單純的故事。如果可以的話,其實很想以「很久很久以前,在某個遙遠的地方……」這樣和時空無涉的句子開頭,不過像《月光》這樣的故事似乎不大適用這種童話故事式的開頭。
最初幻想的場景是個極簡的空間,譬如說荒涼無邊的大漠,或是沒有表情的無名城市。然而,在建構這荒涼場景的過程中,荒涼的緣由漸漸浮現一種可能性:似乎發生過一場戰爭。原本只想用「似乎發生過」這樣模稜兩可的線索來暗示曾經發生戰爭的可能,但後來覺得這種背景設定有點不乾不脆,就索性寫得明朗一點。如果要問為什麼是戰爭的話,我想是基於對未來的一種焦慮吧。這種焦慮或許有點多此一舉,不過我想許多設定類似背景的作品,都或多或少隱藏著這樣的焦慮。
問:本書中,有哪些部分是來自你的真實生活?
答:《月光》中發生的事件都是虛構事件。不過,既然這些事件是從我的腦子裡虛構出來的,它們的源頭應該還是從生活中汲取養分。我想,關於對瘟疫的恐慌,或是特殊事件後長期停電的狀況,應該是許多台灣人的共同記憶,但是《月光》中的瘟疫或停電事件和我所經歷的瘟疫或停電,應該只有某一瞬間對於光線或氣味的描述是相似的。我不太會把真實生活放進小說裡。在台北生活的某個時期,在某些場域進行類似社交的動作時,經常聽見四周的人引用一個又一個人名理論專有名詞。他們有些是真的有研究,另一些則僅止於引用,但這些人和他們說過的話都沒有真的出現在我寫的虛構小說裡。若要說真正在我的生活中發生過的情節,應該是「因為後悔而在回憶中將過去修整得更加光輝燦爛」這件事吧。
問:書中哪些人物原型是你熟識的人物?
答:基本上一個也沒有。我是一個很怕被朋友罵的人,因此絕對不敢將認識的人活生生寫進小說裡。我寫的所有人物都是虛構的。《月光》裡面出現的人物多半是相當極端的典型人物(希望他們還不至於因此太過平板),如果他們的某些行為舉止像是針對特定對象的描寫,那應該是綜合我個人平日在生活中看見的某些路人或非路人的舉止而寫出來的。這些行為舉止平時四處出現在不同的人身上,直到寫作時才被重新綜合歸納在同一個角色身上。這種綜合歸納的動作對我來說是相當有趣的,同時也是寫小說最吸引我的地方之一。活生生的人類不會只是一種典型的表徵,而是許多典型的綜合體,如何製造出類似人類的「配方」,是塑造角色最困難的事情。我想寫小說有趣的地方之一,在於創造出虛構的人物並讓他們做一些虛構的事情。
問:你過去創作過小說嗎?是甚麼動力驅使你寫下這本小說?
答:我從高中開始寫短篇小說。十七歲時第一篇小說被登上雜誌,因為是寫在稿紙上面投稿,我似乎把兩個格子分量的六個點塞進一個格子裡,於是文中所有的刪節號都被誤刊為驚嘆號,也就是「我看著天空……」變成「我看著天空!」之類的,整篇文章的口氣變得很激動,後來雜誌社把它結集出書也沒有改掉,讓我每次看到那本書都覺得很痛苦(尤其那篇小說又寫得不好)。我個人寫東西是很不喜歡用驚嘆號的。在報章雜誌發表過幾篇作品都不太滿意,結果常換筆名。寫小說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有點像是不定期發作的隱疾,發作時就在半夜著魔似地埋頭亂寫,寫完覺得萬分羞愧,不敢讓人看到,於是身邊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我有在寫小說。《月光》是我第一部長篇小說,這幾年「發作」時都在埋頭寫這個,如果要說動力,應該是因為隱疾發作而不得不寫(笑)。
問:可以談談這本小說的創作經過嗎?花了多少時間完成?
答:這篇小說在大學時期以第一人稱敘事零零散散寫了一萬多字然後全部作廢,二○○四年完成相當粗糙的四萬字初稿、二○○五年大量修改情節完成八萬字初稿,而今的十萬字算是第四版。二○○五年我前往法國念書,出發前已經完成小說初稿:溫室的黃金印象,溫室的崩毀。溫室之外的理想,為理想共同奮鬥的伙伴,和理想的破滅。不可挽回的錯誤,無可避免的變質,無能為力的幻滅。然而在南法安頓後忙著處理生活上的大小瑣事,而後又遷移到西北部念大學,課業繁忙,八萬多字的初稿就這樣被擱置一旁。
二○○七年,我從充滿超現實風景的布列塔尼半島轉到巴黎念研究所。用法文讀書和寫論文的經驗,劇烈地改變了我的中文寫作模式。法國人講究邏輯而按部就班的論述模式,讓我想用這樣的條理重新檢視自己那天馬行空的小說,於是打開舊稿,發現留法兩年多以來,看待事物的態度和思考方式已和當年大不相同,於是這些年來思考的事情變成了推動故事情節的動力,小說被改頭換面大整修一番,在二○○八年三月底完稿寄出,此時距離第一次動筆寫下灰色城市印象的那個冬天,應該已經七年了吧。如果不算大學時期作廢的第一版,前前後後也寫了將近四年。
問:開始寫作時,你就知道小說的結局嗎?
答:小說的樣貌最早在心中浮現時,只有第一個畫面和最後一個畫面,一個是主角在雪花飄落中來到城市,另一個是她在雪花飄落中離開城市。第一次飄下的是彩色的冰淇淋,最後一次飄下的是月光。小說最初只有這兩個畫面,至於在來到城市之後到離開城市之前發生了哪些事情,都是後來才慢慢想到的。因此,結局幾乎是第一個確定情節的段落。
至於「飄落的月光」這樣的視覺元素從一開始就是這篇小說相當重要的意象,因此最初連故事內容都還不太確定時,就已經確定小說名稱會叫做月光什麼的。有些電影是因為片尾字幕而美麗,或許《月光》也有點像這樣。蘇在城市中的所有遭遇,或許是因為最後離開城市,看見的雪花從(童真的雙眼看見的)冰淇淋變成(洞悉的雙眼看見的)月光,兩者對照之下有所反思,才顯得有意義。
問:這本創作跟你以前的作品有何不同?
答:我剛開始寫短篇小說時,看的中文小說都是一些詞藻華麗、字句精雕細琢的奇書,當時以為「這樣寫才能叫做小說」,所以也盡可能咬文嚼字地寫東西,形容詞越堆越多,句子越加越長。當時的文藝腔非常重,後來改掉很多。出國是一大關鍵,很多寫中文的學生到了法國,交出去的作業總被法國老師劃上一堆問號表示不懂,通病是「句子長到讓人忘了主詞在哪裡」或是「同一個句子裡混合兩三種不同的概念不知道重點是哪一個」。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假如說我們在描述某個主題時多加上一個形容詞,我們可能會認為這個形容詞可以讓概念更精確,但法國教授卻會覺得你這個形容詞是在已經很繁雜的主題中再加上另一個新的概念讓它更繁雜。
譬如說有個同學提出她的論文主題:「愛欲?孤寂?烏托邦:王家衛的電影世界」之類的,老師說「『愛欲』、『孤寂』和『烏托邦』三個都是很大的主題,你到底要研究哪一個?」當然寫小說和寫論文是不一樣的,不過我覺得在法國接受的寫論文訓練,的確幫助我把《月光》寫成一個概念更加清晰的小說。或許對某些人來說它太過清晰有點嘮叨過頭,不過總比語焉不詳來得好一點。這是我對自己的作品的期望。
問:書中有許多場景描述「同化」狀況,諸如:蘇不肯像父母一樣被城市同化,一直想逃離城市,但是最後一章卻描述蘇贊同將可能染上白症的緹拉送進市立醫院檢查;同樣的,緹拉這個角色也是,從一開始的溫室生活,最後竟也接受城市的安排,這些是否象徵了蘇與緹拉都陷入「同化」的矛盾情節中? 答:我很少用「同化」這個概念來看小說中的人物。
「被同化」是一種被動的態度,其實要或不要,很多時候是選擇的問題。先說緹拉的狀況,她之所以在小說前半部成為對抗市民體制的象徵,是因為她一出生便生活在溫室裡,自然而然便成為溫室的一部分。一開始是緹拉的祖父母選擇讓她成為溫室的一部分,後來是丁丑選擇讓緹拉成為城市的一部分,這些選擇對他們而言似乎都理所當然,他們不過是把自己的價值觀灌輸給緹拉,而緹拉本人從來沒有為自己做過任何抉擇,也沒有試圖去對抗這些他人灌輸給自己的價值觀。
(或許用沙特的說法來說,她是「選擇不去選擇」?)與其說緹拉沒有堅強到足以為自己做抉擇,不如說她從來沒有意識到自己做抉擇的可能性。以「同化」的概念來說,無論是溫室的價值觀或是城市的價值觀,緹拉都是不假思索在身邊的人的引導下被同化的,如果要問她,她或許會說「沒有辦法,狀況就是這樣」。
回頭看蘇的狀況,蘇倒是不停地做抉擇,試圖和城市價值觀保持距離。第四章最後一段的蘇其實是輸給自己內心的軟弱,儘管意志拒絕城市,她依舊是個擁有脆弱人性的人類,會害怕自己染上嚴重的「傳染病」。所以蘇的態度變得模稜兩可而被動,將做抉擇的重責大任推給丁丑,讓丁丑選擇將緹拉送進醫院。蘇鼓勵緹拉進市立醫院的言詞只是為了掩飾心中的不安和罪惡感,其實連蘇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說詞。當緹拉輕蔑地回問蘇是否只是害怕被傳染,印證了蘇其實也像緹拉先前說的「市民都自私自利只想著自己」,蘇才驚覺自己的心態。或許因為這樣,接著第五章便出現蘇「想知道自己的心是不是已經變硬,變成像城市那樣的灰色」。這或許是您說的「同化的矛盾情節」。據說社會化是成長的必經現象,從這方面來說,或許每個剛成年的大人都面臨著這樣的矛盾情節。
問:本書所描述的戰後世界,讓人感覺像在看科幻電影,不知電影是否也影響了你的寫作?若有,又是哪幾部電影呢?
答:我並不認為這篇小說「科幻」……它一點也不科學,頂多是幻想成分多了點(笑)。我想電影應該是深切地影響了我整個人,因為我經常被恥笑是電影蟲,大學四年都泡在電影社,出國念的也是電影。但確切來說究竟是哪些電影影響了哪一部份的寫作,是很難說的。(題外話,你們覺不覺得自從電影發明並日漸普及之後,許多小說書寫都變得視覺化了?)
若真要舉些科幻電影當例子,我想佛列茲朗的「大都會」或Terry Gilliam的「巴西」或許對這篇小說的價值觀有些影響。我個人相當偏好日本科幻漫畫中荒涼的世界觀,高中時最喜歡的漫畫是木城幸人的「銃夢」(第一部),我想《月光》的灰色城市或許有點像廢鐵鎮和沙雷姆的綜合體也不一定。科幻動畫方面,我是押井守的忠實影迷,十幾年來反覆重看他的作品,想必有著非常深切、或許連自己都不自覺的影響。